发布日期:
对话高建群

 ●《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
●《最后一个匈奴》作者高建群  ●高建群现场签售书
●高建群现场签售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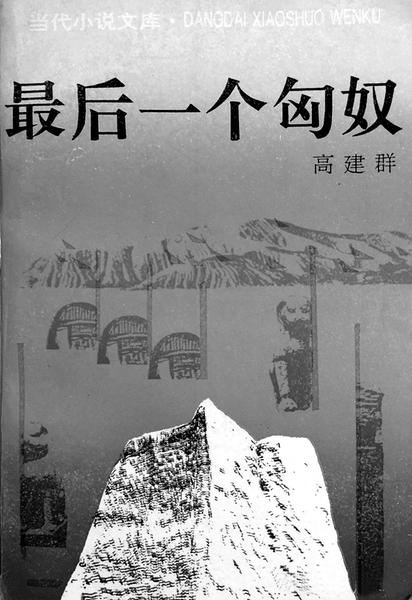
 本报记者 赵秉瑜
本报记者 赵秉瑜 1993年5月19日,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部高原史诗再现了陕北这块土地上匈奴曾留下深深足迹的特殊地域的世纪史,并且与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等作品一起引发了“陕军东征”现象,震动中国文坛。27年后的今天,高建群在延安学习书院阅读空间,与当年同事、挚友,以及延安、榆林的文化学者、文学爱好者们一起重温当年《最后一个匈奴》的问世与创作的艰辛,再话“陕军东征”背后的故事及其深远影响。
五月的延安学习书院苍翠欲滴,夏风习习,满院的书香气让人感到陶醉。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8周年之际,5月19日上午,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兼谈陕北文化专题互动讲座在延安学习书院阅读空间精彩开讲,以此纪念“陕军东征”27周年,纪念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27周年。
1“陕军东征”那些事及其影响
专题互动会现场,高建群向大家饶有兴致地讲述了“陕军东征”这个口号提出的背景和当时所引起的关注。
1993年5月19日上午九点,高建群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提出“陕军东征”这个口号。高建群说,“根据著名文学评论家何振邦先生后来回忆,‘陕军东征’这句话是开会上电梯时,他说出来的,与会女记者韩小蕙第二天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报道,并在大标题用了‘陕军东征’。《陕西日报》在第三天全文转载了这篇报道。这就是新时期中国文坛‘陕军东征’的由来。该座谈会当时由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陕西省委宣传部、延安地委、行署联合召开,今年5月19日正是‘陕军东征’27周年。”
27年前,著名文艺评论家陈荒煤先生因必须参加全国电视剧本评奖颁奖大会,未能出席《最后一个匈奴》在京举行的研讨会,他作了书面发言。陈荒煤先生在书面发言中对《最后一个匈奴》的出版给予祝贺。他在信中说道:“小说接到的时间太晚,来不及看。但是,作为延安的一位文艺战线上的老战士,听到介绍,这部长篇小说写了大革命时期以来的三代人的命运,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时期,这还是过去没有人写过的重要题材,我很高兴!我祝贺这部作品出版,并获得成功!”
27年后,在延安学习书院举行的纪念“陕军东征”学习大讲堂,同样得到了很多知名作家的关注,并发来贺信。
编辑家、评论家、散文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阎纲在贺信中写道:“《最后一个匈奴》晋京的盛况如在目前。27年了,远远跳过速朽期。27年了,它的风采依旧。27年了,人们——特别是陕西读者没有忘记它,了不起啊!”
周明,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冰心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社社长,他在信中写道:“27年前在北京轰动一时的‘陕军东征’,至今在文学界仍是一个历史性的重要话题,一段难忘的记忆。”
“陕军东征”作为27年前文化界的火爆现象,在中国文坛曾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奠定了陕西文坛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引发了人们对于长篇小说的阅读热潮,也在文坛掀起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新时期。后来陈忠实的《白鹿原》改编成了电影、电视剧,《最后一个匈奴》也改编成了电视剧《盘龙卧虎高山顶》。这是继路遥之后,再次振兴陕西文坛的一次有意义的“挥师东征”。
2 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
高建群曾在延安生活、工作了30年,人生和事业的起步都是在延安,对延安充满了感情,他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统万城》都基于陕北古今历史而创作。
匈奴是一个崇拜狼的草原游牧民族,勇猛彪悍、骁勇善战,曾以铁骑征服了广袤的土地,也曾在陕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策马游疆,留下深深的足迹。高原史诗《最后一个匈奴》再现了陕北边陲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一代又一代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高建群当年被誉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
延安文化学者杨葆铭,作为高建群当年在延安日报社的同事、挚友,他对高建群的作品推崇有加。他说,高建群对现代文学有着巨大的贡献,是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在陕北这片厚重的土地上,面对历史的沉淀,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面对手稿曾经丢失,高建群需要进行二度创作,全凭记忆把丢失的五十万字重新完成,如果没有毅力,没有对文学的挚爱以及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是做不到的。如今,距离作品首次发表已经过去27年了,27年足以使人忘记好多事情,唯独《最后一个匈奴》在文学界经常有人谈起,可以说是“不朽”了。本书所传递的精神以及对世界的理解,将代代相传。
当年,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手稿丢失,这也成为《最后一个匈奴》在业内的一段佳话。在延安作家苏世华眼里,高建群是一位非常善良厚道的兄长,同时又有着超乎常人的坚强意志,是真正用生命创作的作家。面对几十万字的初稿丢失,可以说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之后又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写出来,确确实实是在“把自己的伤口舔干净,再往山口上爬”。
3《最后一个匈奴》创作的辛酸艰难
面对来自榆林、延安的文化学者、文艺爱好者,高建群与大家一起分享了《最后一个匈奴》的创作过程,以及它背后的故事。然而对于高建群而言,他多么不愿意回忆这部长篇小说在创作中所经历的苦难。
十年磨一剑,《最后一个匈奴》问世。在谈到创作《最后一个匈奴》时,高建群表示,他整整用了10年去做准备工作,而写作其实只用了1年零10天。
1979年4月,陕西省作协在西安开了恢复活动后的第一次创作会,延安有臧若华、张弢和高建群参加。会议期间,臧若华和高建群约好要写一部陕北题材的小说,她甚至提供了大量的细节,包括《最后一个匈奴》中“高粱面饸饹羊腥汤”事件,还有那个剪纸的小女孩等。
高建群说,会议后这个题材一直萦绕在自己的脑海中,再也无法丢开,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后,高建群开始了《最后一个匈奴》素材的搜集及准备工作。
1989年,为这部小说整整筹备了10年的高建群接到了一份长篇小说的约稿合同,他当即就签了《最后一个匈奴》的出版合同。1991年5月,高建群开始闭门创作。1992年6月13日,呈现陕北边陲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和一代又一代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的《最后一个匈奴》终于问世。当作品完成的那一刻,高建群哭了,他对自己说:“你是不可战胜的!”一年多一点的创作,他抽了一百多条烟,瘦了十三斤,掉了三颗牙齿。现在肉又重新回到了身上,只是牙齿永远没有了。
“在那一年多的时间内,我就像一架失控的航天器、一个植物人一样地生活着,我生怕我不能把自己的沉重思考告诉人类,就撒手长去。”高建群说。
谈到为何书名要叫《最后一个匈奴》时,高建群表示,意欲写一部二十世纪的高原史诗,意欲寻找二十世纪高原历史的行动轨迹,当然要注意到陕北的大文化现象,要研究、归纳,透过层层迷雾找到本质的东西,这样才能破译许多大奥秘。陕北的本土文化顽强地从这块荒僻之地生长出来,给这种文化以最重要影响的,是各民族文化的融汇,而在融汇中匈奴文化的影响显然是最为重要的一次。“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奇妙地结合,显示了这块高原文化因素的主要特征。”高建群说,这也许就是要选定“最后一个匈奴”作为书名的缘由所在。
出生在关中平原的高建群对陕北情有独钟,他把自己的写作和思考与三条河紧紧地关联到一起,他说:“渡过了我卑微和苦难少年时代的渭河,在岗哨和马背上把青春年华抛洒的额尔齐斯河和我走向成熟、成功的延河。正是这三条河构成了我文学作品的主要源泉和根基。”延河是三个精神家园之一,他对陕北更是情有独钟。
每到延安,出生于关中平原的高建群似乎就有讲不完的话。他说,从少时在延安生活、上学,到1977年退役又回到延安工作,他与延安一直紧密连接,也正是在延安这片热土上,有了《最后一个匈奴》这部作品。
在高建群看来,“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史是以另外的一种形态存在着的,这形态就是,每当那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华文明,走到十字路口,难以为继时,于是游牧民族的踏踏马蹄便越过长城线,呼啸而来,从而给停滞的文明以新的‘胡羯之血’。这大约是中华古国未像世界上另外几个文明古国那样,消失在历史路途上的全部奥秘所在。”
高建群说,《最后一个匈奴》出版后,能受到一些前辈的认可,他感到很欣慰。同时,这部书直到现在,能让众多的读者喜欢,尤其是陕北文学爱好者的喜爱,这让他诚惶诚恐,他觉得他是为读者而活着,为他们而写作。他最后告诉延安、榆林的文学创作者:要做好经受苦难的准备,警惕社会庸俗性,走出浮躁和庸俗,沉静下来,让自己的作品走出延安、陕西,放眼全国、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