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被门口咬伤的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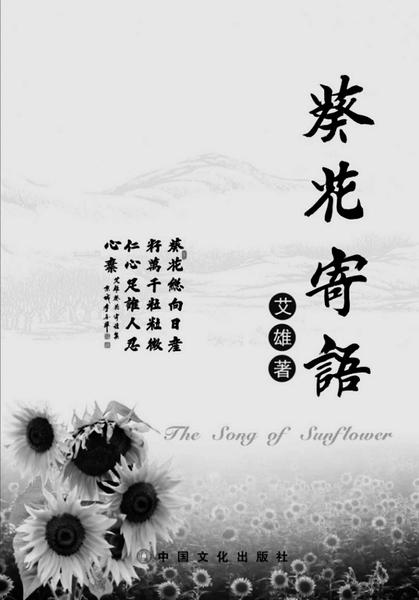 袁茂林
袁茂林 作者简介
乔艾雄,陕西佳县人,毕业于延安大学中文系,中国近代史研究生学历。曾在政府计划、广电部门从事经济、重点工程调查、信息内参编辑、文秘等工作。先后在省市报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数十万字,其中长篇报告文学《穿越黄土地》获陕西省计委系统特别奖。
作品介绍
《葵花寄语》共收录80多首诗作,作者用饱含激情的笔触,满腔热情地与自然、社会上存在的现象对话,展现生存体验的原生态,传递生命的脉搏,升华揭示了事物存在的本质和蕴藏的真谛,抒写了心路历程。
诗集共七辑,其中《太阳血》《金色大河的记忆》两辑,主要抒发对祖国母亲、对黄河儿女的挚热爱恋和歌颂。《延安的故事》则是对革命圣地一草一木的含泪敬仰,用心灵触摸这片红色泥土折射出的阳光色彩,情真意切,感人至深。《坐在三月的秋千上荡漾》《一对柏林水桶的故事》《一只蛹的旅行》三辑,深刻表达生命历练的痛苦与成熟,质感细腻,触及灵魂。第七辑《飘香的苜蓿地》是作者对纯真爱情的热情歌颂。
一
生与死的夹缝 挤压出背叛的筹码
作为学中文出身的乔艾雄写诗,按理说应该就像种下小麦长出麦苗,月亮落了太阳升起,春天来了秧苗出土一样自然,自然的似乎不值得人们联想到其逻辑意义的存在。然而,现实并不如此。乔艾雄可以折叠的思想之光即从平凡的生活折射出五色诗意,这个过程却演绎了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从理性到非理性的传奇。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社会现象存在,那就是做什么事的不一定爱什么事,能做了什么事的不一定能做上什么事。于是,学医的从了政,从政的为了文,从文的经了商……乔艾雄当初亦是如此,拿到文学院的文凭时,似乎也不曾想到自己能够与诗歌结缘,过上一种理智含量极高的人文生活。而是和芸芸众生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甚至忘记了自己尚为一具活体生物,把自己的前途和命运自觉不自觉地拱手交给那个既熟悉又陌生、既无奈又依赖的“社会”去主宰、去驾驭、去摆布,“茫然的心/栖落城市/像一只灰灰的麻雀/卷缩于灰暗廉价的弃窝/在城市低空的屋檐下/东一程、西一趟/南碰壁、北撞墙……”(《找工作》)。就这样,开始了复制他人生活样板,重叠岁月春夏秋冬,占卜自己终极归宿的生存本能活动,用忙碌的工作包装着浮躁的生活。当忙碌与浮躁成为一种习惯后,日子便平静了下来,平静得像雪花和花瓣落地且能听出叮当有声。
2009年初春的一天,乔艾雄“一个七尺男儿的肉体/被一名无照驾驶员/重重地按倒在大街/工程运土车蛮横地蹂躏/他的肉体躺在自己的血泊里……”(《站在公疗办的门口》)。乔艾雄的世界以突然的血光之灾的形式,以重型机械把肉体蹂躏得体无完肤的结果,彻底颠覆。然而,就在疾速飞驰的重型机械和血肉之躯零距离间关于文明与野蛮的对话中,奇迹出现了:“其实,蹂躏过程最后一瞬/他很愉悦很骄傲很有快感/甚至不觉得痛/凌空飞翔坠落好爽好刺激/丝毫没有被蹂躏的感觉/因为出窍的灵魂/拒绝了死神的盛情邀请……”(《站在公疗办的门口》),文明战胜了野蛮,血肉之躯击溃了钢铁机械。乔艾雄奇迹般地活了,只是被生与死通道上的公共门口重重地咬了一口。
人,所有的承受都来自于另一端的不能承受。把一只青蛙直接放进热水锅里,求生的欲望在一瞬间爆发的超自然力量,就会使青蛙箭一样飞出锅外。如果把一只青蛙放进冷水锅里,慢慢地加温,青蛙并不会立即跳出锅外,水温逐渐提高的最终结局是青蛙被煮死,因为当水温高到青蛙无法忍受时,它已经来不及,或者没有能力跳出锅外了。这一现象告诉我们:有些突变事件,往往容易引起人们的警觉,而易致人于死地的却是在自我感觉良好的情况下,对实际情况的逐渐恶化,没有清醒的察觉。艾雄先生就如同“青蛙现象”一样,当他怀着平淡心情突遇死亡的降临,从自己的血泊中站起来第一个表现是从容地笑,他为自己从“开水锅”里奔出的奇迹而庆幸。他这一笑已不是一个单纯的表情概念了,而是一种生命意识和存在意义在一瞬间获得的觉醒。
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即含精神与物质为一体。人与他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智慧和道德浇灌的灵魂。一个一旦失去智慧和道德浇灌的灵魂,无异于行尸走肉。看过种种纷繁的事和体验过塞满多半人生的坎坷无常之后,一次与死神的际遇使乔艾雄有了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茅塞顿开。任尔红尘滚滚,我心自有葵花。
所有的建树都是建立在对过去颠覆的基础之上,所有的创新也都是以背叛为代价的社会实践活动。经历了一次对生命的终极体验,乔艾雄读懂了什么是失败、不幸、挫折、痛苦、追求、亲情、友情、成功、幸福。并研习痴迷上了《圣经》里的《诗篇》,对整个世界、万物苍生给予了宗教般的虔诚。这种对人性终极关怀的情愫,终于以个人诗歌的方式得以最佳的发现、开慧、释怀、背叛和自我拯救,自立自强。
二
诗歌的镜子 折射着人性的光辉
在“揉搓出打了折的存在/支撑着打了折的生活”(《石碾》)中,乔艾雄以纯粹原始的目光冲撞着既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说他对这个世界陌生吧?毕竟以知识分子的姿态生活了几十年;说他对这个世界熟悉吧?为什么生活的厚度和生命的宽度以前就没有仔细测量过?于是,熟悉中的陌生弥漫了他存在的整个空间。他像一个虔诚的教徒,以至上至高的情怀重新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一朵朴素的山丹丹花,一抹或红或白的云,一条涓涓溪流或者汹涌澎湃的河,一条曾经讨厌过的狗或者小时候用弹弓射杀过的麻雀,一只破旧的水桶或者一片落叶,满地的庄稼或者漫卷的风雪,以及所有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包括爱他、他爱甚至仇视他和他仇视的人……一切的存在何以转眼间变得那么鲜活灵动,那么可亲可爱,那么叫人心疼、辛酸和兴奋。背叛了的思想在病房点点滴滴药液的灌溉下蓬蓬勃勃地疯长。学中文的本能使他自然地撒开如网的方格稿纸,在记忆的深井里打捞着属于自己也属于社会的真善美。在这样一个非常的季节里,凝固的大山活了,以往的历史重演,连阳光也可以折叠。
从“带着赤色革命的胎记/来到了充满饥饿和口号的年代”(《中85,我们共同的名字和记忆》),“枝头不该被抹掉的碧绿/那些年被父亲长茧的大手/一片片揪落/浮现在饥饿年馑的碗里”(《榆钱儿》)开始,以“只祈求大地/能给与一寸土壤;只祈求天空/能落下几滴雨水;只祈求太阳/能给予一尺阳光”(《豆芽儿》)的最低要求,挣扎到“分地单干和责任制来到身边/我们碗里的成色渐渐好起来”(《中85,我们共同的名字和记忆》),经历了“农村依然包围着城市/但在城市面前/一脸困惑陷入包围/城市在霓虹灯下笑着乐着/农村在污染的河畔愁着苦着”(《农村与城市》)的世态炎凉,到《一只蛹的旅行》《谷子的形象》《浮萍》的洞幽深邃,长达400余行的《金色大河回忆》的壮怀激烈,及至《祖国,我和你永不分离》《印象西安》《飘香的苜蓿地》的慷慨浪漫……如同大地亿万年积累的能量突然爆发,乔艾雄文学生命中的壮观景象展现了,也就是这本《葵花寄语》。
凡美文佳作的根本要义是做到心境合一,心要发情,情要融境。要问艾雄的诗歌创作有什么突破?我认为最大的突破点是诗我界线的消失,达到了诗与人融为一体的境界,使他生活的分值因诗的意境而提高,诗的审美高度因人的品位而升华。那些油然而发的情感有喜、有忧,有歌、有泣,扣人心弦。构建的意境有古、有今,有虚、有实,逼真妥帖。从《葵花寄语》里的《浮萍》《北国的冬季》《乡愁》《乡恋》《打谷场 老井 三爷村里人》《豆芽儿》《榆钱儿》《石碾》《怀念枣树》《一颗草莓》《别碰那株玫瑰》《一对柏木水桶的故事》等等,从这些“斑驳的字句会哭出泪花”(《宇宙信笺》)的诗篇里,我读到了对伟大的向往、对崇高的敬畏、对神圣的虔诚,读到了批评的勇气和质疑的精神,人道的情怀和信仰的热忱,高贵的气质和人格的魅力。这几多令人欣悦的大美和为何而写得明白,恰恰是当今许多所谓诗人“哪怕是诗人也要创造一种十分诡异/需研究者才能大致弄懂的产品”(《浮萍》)的软肋。读《无缘的岸》《葵花寄语》《相思泪》《秘密》《约》《红毛衣》《记忆问心》等诗,从中可见席慕容诗作的婉约细腻和伤怀;读《恋者》便可见舒婷《致橡树》的崇高爱情;读《印象西安》《镇北台》《啊,窑》《黄河与高原远征》等,何尝没有诗人李白、东坡、余光中、洛夫佳作的恢宏豪迈;读《祖国,我和你永不分离!》更有郭沫若诗歌的眷眷赤诚;读《一对柏木水桶的故事》《打谷场老井三爷村里人》《涝池》,也有艾青叙事诗的亲切实在;读《金色大河的回忆》(诗人长篇诗作的局部)便使人仿佛置身于沈从文先生构建的湘西《边城》小说故事里的恬静;读《梦的草原》《飘香的苜蓿地》恰在国人神往的爱情里品味出浪漫无边的异国风情,比《乘着歌声的翅膀》(海涅)、《孤独的收割人》(华兹华斯)意境更迷人陶醉,却又丝毫不失东方诗歌的神韵。诗人天生的禀赋,广泛的阅读,怀揣研读《圣经》诗篇一路走向诗坛,幸甚至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