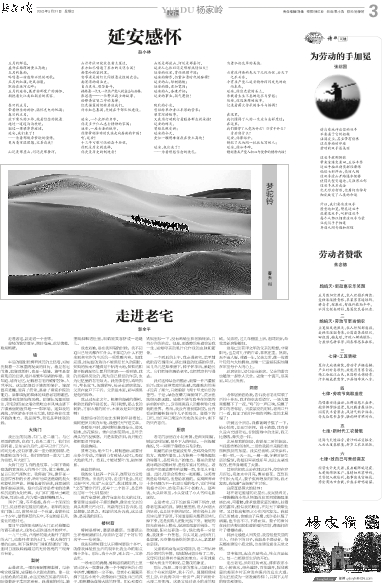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5月21日
走进老宅
走进老宅,就走进一个世界。
曾经的繁华落尽,满目疮痍,荒草葳蕤,残垣断壁。
墙
午后的暖阳抚摸着淡黄的土坯墙,宛如抚摸着一本厚重的发黄的日历。墙是老宅的墙,就像我的姓,也是一堵墙。墙里是寂寞荒凉的世界,墙外是繁华似锦的华章。我知道,墙有记忆,记载着老宅的酸甜苦辣,人世浮沉。这记忆得益于墙泥的保护。墙泥混有麦糠,便有了筋骨,具备了看家护院的能力。涂抹墙泥的墙体延续着老宅的雕塑,也雕塑着我惆怅的灵魂。即便狂风暴雨如注,老宅的四面之墙依然屹立在凤凰山脚下古镇索堡的发祥地——郭家垴。宛如我的魂魄,尽管游走于阳光大地,却定格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是风筝,老宅是牵挂我的线。
大街门
我出生的院落,有门,是二道门。与它照面的院落,也有门,也是二道门。他们同宗同祖,是东寨的后代,却早已分门另户。时间无考,没有家谱,如一筐分散的蒜瓣,是熟悉独立的个体。他们拥有同一道大门,因为临街,叫大街门。
大街门无门,有的是故事。只剩下青砖砌就的宽厚高大的两个门垛,做工精细,足显昔日的气派恢宏。我仰视门垛,像仰视一位忠厚淳朴的长者,聆听他讲述燃烧的战火和怒吼的声音。伴随长者的讲述,我宽阔的胸怀波涛汹涌。发白的青砖是老宅的沧桑和沉淀的太阳光辉。大门和门楼早已藏进故事,写进历史,作为爱国题材警醒后人。
两个门墩,齐齐整整,各有一个深深的门臼,见证着老宅曾经的烟火。老年的我坐在门墩上面,曾经坐过一个孩童,也曾坐过一个少年,望着湛蓝的天空,不变的是日月,变化的是时光。
夏日午后的阳光晒得大门正对着堰边的青石条冒火,我的心却跌进冰冷的世界。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炮火轰开了祖国的大门,也轰开老宅的大门,一把火烧尽门楼的血肉,剩下强悍的门垛和坚硬的门墩,连同日寇铁蹄践踏过的光滑锃亮的三级青石台阶。
梨树
走进老宅,一眼就看到那棵梨树。母亲唤它秋薄梨,皮薄核小水甜水甜的。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妪,永远定格在孤寂的风中,盼望着游子常回家看看。我进来的时候,她
把眼泪咽进肚里,眼睛被笑容挤成一道缝儿。
我走近她,是在我闲暇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忙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把光顾老宅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我知道,这短暂的造访不能满足长久的期盼,短暂的秋雨不能满足干枯的大地,短暂的相聚不能满足经年累月的相思……看到她,我的灵魂是哭泣的,既为自己曾经的忤逆,也为记忆里的老宅烟火。我仿佛看到,鸡鸣狗叫,草长莺飞,兔跳猪哼,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窗户下干活。父亲是木匠,起早摸黑是他的宿命。
我已过天命之年。粗细约海碗的梨树,树龄比我的年龄还长。有时我想,那么长的树龄,才那么粗的树干,木质该是如何坚硬啊!
我想追寻的历史比梨树的年龄要长。梨树把岁月刻在年轮,我把时光写进文章。
春暖花开时,满树梨花挂满枝头,微风轻拂,落花缤纷。雪白的梨花带雨,是母亲满头的白发飘落。只是梨花依旧,我只能在相框里泪目母亲。
我很纳闷。
贫瘠之地,绝少有土,树根遒劲,需要付出多少劳动,才能错节有致钻入碎石,吸取大地的乳汁。然后,才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我也很纳闷。
我的女儿抚养一个孩子,连带双方父母都很费劲。而我的父母,走过旧社会,见证过新中国,吃过“大食堂”、熬过赖年景,与“文革”健步同行,抚养十二个孩子,是怎样度过每一个日月星辰?
我背靠梨树,像背靠流年似水的过往,像背靠母亲瘦小干瘪的胸膛,像坐在父亲的肩头观看元宵花灯。高悬的日月告诉我,这是想象,是思念。孤寂的风告诉我,这是成熟,是灵魂的回归。
椿树菇
椿树是椿树,蘑菇是蘑菇。当蘑菇出生在椿树跟前时,母亲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椿树菇。
我认识椿树菇比认识椿树要晚十多年,就像我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比我生命的起点晚十多年。那年,我十六岁,刚上高一,父亲去世。
一场雨后的清晨,椿树跟前腐烂的土里冒出好大一簇蘑菇,像一个个褐灰色的小雨伞挤着,嫩嫩的一尘不染。母亲小心翼翼采摘下这些小雨伞,就像她自己接生自己的孩子,剪断蘑菇连接大地的脐带。用心和爱在铁锅里炒一下,没有鸡精生抽老抽蚝油,只有少许的油盐。但是,那香醇的味道弥漫我一生,宛如母亲的乳汁化作我的血脉和筋骨。
一个雨后的上午,我走进老宅,院里铺就的青石缝隙间,挤出绿色的旺盛的杂草。风儿鸟儿把草种播下,种子怀孕后,渐趋长大。它们把绿色赐给老宅,也把荒凉书写进去。
我对这种绿色的憎恶,就像一件古董被玷污;我对这种荒凉的伤感,就像晚归的燕子没有了巢穴,只能重新飞翔于星光灿烂的苍穹。于是,绿色在镰刀面前倒下,荒凉也跑得无影无踪。疲惫不堪的我坐在坍塌的房前的台阶上,身旁挺拔高大的椿树转化成我的世界。然而,我没有看到椿树菇,没有看到把椿树菇当作儿子的母亲。像撕下的日历,他们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剩下的只有悲伤。
厨房
老宅的厨房在小院南侧,是两间明厦。厨房又叫饭厦,是乡下人的叫法。一间饭厦做饭,另一间用于储藏农具及杂物。
明厦的前身是置放柴草、垒鸡窝兔窝的地方。鸡窝在墙角,上方挂着一个荆条编织的破篓儿,是母鸡生产的地方。篓里的麦秸被母鸡卧成椭圆形,是经年累月的积淀。老母鸡产完蛋总要咕咕炫耀一番,生怕人不知道。此时,母亲会奖赏它一把粗粮。这奖赏既是给母鸡的,也是给家庭的。兔窝圈养着十多只颜色不一机灵可爱的兔子,它们伴随我整个初中,给我带来不小的收入。那些钱,大头给家里,小头变成了小人书和电影画报。
走进老宅,目下的厨房只剩下锅台,就像老宅孤寂的我。锅灶里墨黑,是人间烟火的足迹,也是抹不掉的记忆。掉在锅台上的泥块儿源于房顶,不知道是阳光跟着泥块儿掉下来,还是泥块儿把阳光拽下来。暖暖的阳光在锅台上移动,想温暖孤寂的锅灶。可谁知道,阳光每移动一步,锅灶就多一分沧桑,我就多一分苍老。仰头可见,房顶有几处窟窿,天空像母亲烙的饼那么大,紧紧贴在房顶。
父亲将鸡窝兔窝变成厨房,是二哥结婚后分家时的事情。现成的厨房分给了二哥,父母和我总得有个做饭的地方。分家就像一棵大树生开的树杈,是繁茂的象征。
那年,就是二哥分家的那年,也是我们哥三个分家的那年,我十五岁。舅舅把我喊到上房,让我挑中间一份房产,剩下两份让大哥二哥抓阄。这是父母对老小的我的照顾。父亲说,过几年翻盖上房,连同厨房,给我盖新房娶媳妇。
这是已近花甲之年的父亲的理想,非常阳光,也是对儿子的许诺,非常庄重。然则,天不遂人愿,时隔一年,父亲去世,像一枚落叶轻轻与大地拥抱,却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家里每个人的心上。
厨房依旧,没有变成新房。父亲的诺言也随他一起步入天堂。就像一个谎言,很美丽,却无比忧伤。
洞房
老邻居捎信给我,告诉我老宅北屋塌了后约十多天,我才得空去看望它。一场大暴雨整整下了一夜,“咚”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梦中的老邻居。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两口开门一看,验证了他们半夜的判断:我的北屋塌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像被蝎子蜇了一下,钻心地疼,却无可奈何。说不清楚,我有多久没有光顾老宅,看到废墟中的北屋,我无比落魄,像失恋一样。
北屋是我的洞房,也曾是二哥的洞房。当我要结婚的时候,二哥给我腾出来搬到他抓阄抓到的东屋。我买把板刷,买来涂料,一刷一刷,一天一天,一遍一遍,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把旧屋刷成新屋,把过去刷成现在,把单身刷成了夫妻。
曾经的初恋止步在洞房之外,停留在岁月深处,宛如水中月亮,雾里看花。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妻子疾病缠身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抱着“金饭碗”在讨吃。
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站在老宅废墟的北屋前,我突然看见,一棵嫩嫩的小草从坍塌的房顶间隙倔强地挤出来,弯着腰,像承载着家庭的重担,挂着夜的露珠,酷似我的眼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又好似我顿悟之心在闪闪发光。我被自己所感动,也感动了病魔,或许是征服了病魔,也未尝不可,不得而知。妻子的痛苦在我们夫妻如胶似漆的爱情面前,像霜打的叶子慢慢枯萎。
洞房花烛是人间天堂,我曾经是天堂的主人。但余下的日子,我就是个建设者。每天都在建设小康之路,也在建设通往天堂之路。
世事轮回,起点亦是终点,终点亦是起点。每一点都是新生活的开始。
走出老宅,满眼红砖青瓦,排排农家小院,小桥流水,绿色遍野,百花盛开,脱贫致富的美丽乡村正奋进在振兴的康庄大道。老宅已经成为一张发黄的相片,只剩下无尽的留恋和惆怅。
曾经的繁华落尽,满目疮痍,荒草葳蕤,残垣断壁。
墙
午后的暖阳抚摸着淡黄的土坯墙,宛如抚摸着一本厚重的发黄的日历。墙是老宅的墙,就像我的姓,也是一堵墙。墙里是寂寞荒凉的世界,墙外是繁华似锦的华章。我知道,墙有记忆,记载着老宅的酸甜苦辣,人世浮沉。这记忆得益于墙泥的保护。墙泥混有麦糠,便有了筋骨,具备了看家护院的能力。涂抹墙泥的墙体延续着老宅的雕塑,也雕塑着我惆怅的灵魂。即便狂风暴雨如注,老宅的四面之墙依然屹立在凤凰山脚下古镇索堡的发祥地——郭家垴。宛如我的魂魄,尽管游走于阳光大地,却定格在生我养我的地方。我是风筝,老宅是牵挂我的线。
大街门
我出生的院落,有门,是二道门。与它照面的院落,也有门,也是二道门。他们同宗同祖,是东寨的后代,却早已分门另户。时间无考,没有家谱,如一筐分散的蒜瓣,是熟悉独立的个体。他们拥有同一道大门,因为临街,叫大街门。
大街门无门,有的是故事。只剩下青砖砌就的宽厚高大的两个门垛,做工精细,足显昔日的气派恢宏。我仰视门垛,像仰视一位忠厚淳朴的长者,聆听他讲述燃烧的战火和怒吼的声音。伴随长者的讲述,我宽阔的胸怀波涛汹涌。发白的青砖是老宅的沧桑和沉淀的太阳光辉。大门和门楼早已藏进故事,写进历史,作为爱国题材警醒后人。
两个门墩,齐齐整整,各有一个深深的门臼,见证着老宅曾经的烟火。老年的我坐在门墩上面,曾经坐过一个孩童,也曾坐过一个少年,望着湛蓝的天空,不变的是日月,变化的是时光。
夏日午后的阳光晒得大门正对着堰边的青石条冒火,我的心却跌进冰冷的世界。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的炮火轰开了祖国的大门,也轰开老宅的大门,一把火烧尽门楼的血肉,剩下强悍的门垛和坚硬的门墩,连同日寇铁蹄践踏过的光滑锃亮的三级青石台阶。
梨树
走进老宅,一眼就看到那棵梨树。母亲唤它秋薄梨,皮薄核小水甜水甜的。像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妪,永远定格在孤寂的风中,盼望着游子常回家看看。我进来的时候,她
把眼泪咽进肚里,眼睛被笑容挤成一道缝儿。
我走近她,是在我闲暇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忙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不把光顾老宅作为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但我知道,这短暂的造访不能满足长久的期盼,短暂的秋雨不能满足干枯的大地,短暂的相聚不能满足经年累月的相思……看到她,我的灵魂是哭泣的,既为自己曾经的忤逆,也为记忆里的老宅烟火。我仿佛看到,鸡鸣狗叫,草长莺飞,兔跳猪哼,母亲在厨房做饭,父亲在窗户下干活。父亲是木匠,起早摸黑是他的宿命。
我已过天命之年。粗细约海碗的梨树,树龄比我的年龄还长。有时我想,那么长的树龄,才那么粗的树干,木质该是如何坚硬啊!
我想追寻的历史比梨树的年龄要长。梨树把岁月刻在年轮,我把时光写进文章。
春暖花开时,满树梨花挂满枝头,微风轻拂,落花缤纷。雪白的梨花带雨,是母亲满头的白发飘落。只是梨花依旧,我只能在相框里泪目母亲。
我很纳闷。
贫瘠之地,绝少有土,树根遒劲,需要付出多少劳动,才能错节有致钻入碎石,吸取大地的乳汁。然后,才能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我也很纳闷。
我的女儿抚养一个孩子,连带双方父母都很费劲。而我的父母,走过旧社会,见证过新中国,吃过“大食堂”、熬过赖年景,与“文革”健步同行,抚养十二个孩子,是怎样度过每一个日月星辰?
我背靠梨树,像背靠流年似水的过往,像背靠母亲瘦小干瘪的胸膛,像坐在父亲的肩头观看元宵花灯。高悬的日月告诉我,这是想象,是思念。孤寂的风告诉我,这是成熟,是灵魂的回归。
椿树菇
椿树是椿树,蘑菇是蘑菇。当蘑菇出生在椿树跟前时,母亲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椿树菇。
我认识椿树菇比认识椿树要晚十多年,就像我体验到生活的艰辛比我生命的起点晚十多年。那年,我十六岁,刚上高一,父亲去世。
一场雨后的清晨,椿树跟前腐烂的土里冒出好大一簇蘑菇,像一个个褐灰色的小雨伞挤着,嫩嫩的一尘不染。母亲小心翼翼采摘下这些小雨伞,就像她自己接生自己的孩子,剪断蘑菇连接大地的脐带。用心和爱在铁锅里炒一下,没有鸡精生抽老抽蚝油,只有少许的油盐。但是,那香醇的味道弥漫我一生,宛如母亲的乳汁化作我的血脉和筋骨。
一个雨后的上午,我走进老宅,院里铺就的青石缝隙间,挤出绿色的旺盛的杂草。风儿鸟儿把草种播下,种子怀孕后,渐趋长大。它们把绿色赐给老宅,也把荒凉书写进去。
我对这种绿色的憎恶,就像一件古董被玷污;我对这种荒凉的伤感,就像晚归的燕子没有了巢穴,只能重新飞翔于星光灿烂的苍穹。于是,绿色在镰刀面前倒下,荒凉也跑得无影无踪。疲惫不堪的我坐在坍塌的房前的台阶上,身旁挺拔高大的椿树转化成我的世界。然而,我没有看到椿树菇,没有看到把椿树菇当作儿子的母亲。像撕下的日历,他们早已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剩下的只有悲伤。
厨房
老宅的厨房在小院南侧,是两间明厦。厨房又叫饭厦,是乡下人的叫法。一间饭厦做饭,另一间用于储藏农具及杂物。
明厦的前身是置放柴草、垒鸡窝兔窝的地方。鸡窝在墙角,上方挂着一个荆条编织的破篓儿,是母鸡生产的地方。篓里的麦秸被母鸡卧成椭圆形,是经年累月的积淀。老母鸡产完蛋总要咕咕炫耀一番,生怕人不知道。此时,母亲会奖赏它一把粗粮。这奖赏既是给母鸡的,也是给家庭的。兔窝圈养着十多只颜色不一机灵可爱的兔子,它们伴随我整个初中,给我带来不小的收入。那些钱,大头给家里,小头变成了小人书和电影画报。
走进老宅,目下的厨房只剩下锅台,就像老宅孤寂的我。锅灶里墨黑,是人间烟火的足迹,也是抹不掉的记忆。掉在锅台上的泥块儿源于房顶,不知道是阳光跟着泥块儿掉下来,还是泥块儿把阳光拽下来。暖暖的阳光在锅台上移动,想温暖孤寂的锅灶。可谁知道,阳光每移动一步,锅灶就多一分沧桑,我就多一分苍老。仰头可见,房顶有几处窟窿,天空像母亲烙的饼那么大,紧紧贴在房顶。
父亲将鸡窝兔窝变成厨房,是二哥结婚后分家时的事情。现成的厨房分给了二哥,父母和我总得有个做饭的地方。分家就像一棵大树生开的树杈,是繁茂的象征。
那年,就是二哥分家的那年,也是我们哥三个分家的那年,我十五岁。舅舅把我喊到上房,让我挑中间一份房产,剩下两份让大哥二哥抓阄。这是父母对老小的我的照顾。父亲说,过几年翻盖上房,连同厨房,给我盖新房娶媳妇。
这是已近花甲之年的父亲的理想,非常阳光,也是对儿子的许诺,非常庄重。然则,天不遂人愿,时隔一年,父亲去世,像一枚落叶轻轻与大地拥抱,却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家里每个人的心上。
厨房依旧,没有变成新房。父亲的诺言也随他一起步入天堂。就像一个谎言,很美丽,却无比忧伤。
洞房
老邻居捎信给我,告诉我老宅北屋塌了后约十多天,我才得空去看望它。一场大暴雨整整下了一夜,“咚”的一声巨响,惊醒了梦中的老邻居。天蒙蒙亮的时候,老两口开门一看,验证了他们半夜的判断:我的北屋塌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像被蝎子蜇了一下,钻心地疼,却无可奈何。说不清楚,我有多久没有光顾老宅,看到废墟中的北屋,我无比落魄,像失恋一样。
北屋是我的洞房,也曾是二哥的洞房。当我要结婚的时候,二哥给我腾出来搬到他抓阄抓到的东屋。我买把板刷,买来涂料,一刷一刷,一天一天,一遍一遍,怀着对新生活的憧憬,我把旧屋刷成新屋,把过去刷成现在,把单身刷成了夫妻。
曾经的初恋止步在洞房之外,停留在岁月深处,宛如水中月亮,雾里看花。直到孩子们长大成人,妻子疾病缠身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抱着“金饭碗”在讨吃。
这简直是莫大的耻辱!
站在老宅废墟的北屋前,我突然看见,一棵嫩嫩的小草从坍塌的房顶间隙倔强地挤出来,弯着腰,像承载着家庭的重担,挂着夜的露珠,酷似我的眼泪,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又好似我顿悟之心在闪闪发光。我被自己所感动,也感动了病魔,或许是征服了病魔,也未尝不可,不得而知。妻子的痛苦在我们夫妻如胶似漆的爱情面前,像霜打的叶子慢慢枯萎。
洞房花烛是人间天堂,我曾经是天堂的主人。但余下的日子,我就是个建设者。每天都在建设小康之路,也在建设通往天堂之路。
世事轮回,起点亦是终点,终点亦是起点。每一点都是新生活的开始。
走出老宅,满眼红砖青瓦,排排农家小院,小桥流水,绿色遍野,百花盛开,脱贫致富的美丽乡村正奋进在振兴的康庄大道。老宅已经成为一张发黄的相片,只剩下无尽的留恋和惆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