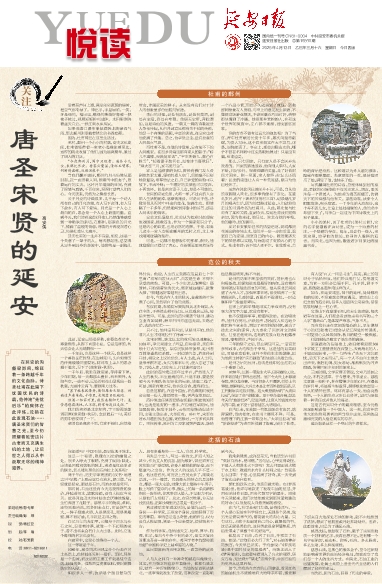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4月13日
唐圣宋贤的延安


 高安侠
高安侠 在延安的沟壑梁峁间,绵延着一条跨越千年的文化血脉。诗圣杜甫在此留下忧国忧民的诗篇,范仲淹“先忧后乐”的胸怀在此淬炼,沈括在此发现石油……唐圣宋贤们的智慧之光,至今仍照耀着延安这片古老而又充满生机的土地 ,让后世之人得以从中汲取无尽的精神滋养。
杜甫的鄜州
沿着葫芦河上溯,两岸郁郁葱葱的绿树,把空气都染绿了。伸出手,手是绿的,一笑,牙是绿的。稻田里,嫩绿的秧苗好像被一把梳子梳过,规规矩矩排列成阵。水田里倒映着蓝天白云,一派江南水乡风景。
如果说壶口瀑布象征着陕北的豪迈气质,那么鄜州则承载着陕北的书香底蕴。
因为,杜甫曾经在这里生活过。
羌村,鄜州一个小小的村落,安史之乱期间,杜甫曾经带着一家老小逃难流落至此。宽厚的陕北收留了他们,因为远离繁华,躲过了胡人的刀兵。
“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
当我们翻开唐诗,鄜州的月亮仿佛从那时起,就一直照着人间,照着闺中的妻子,照着远行的丈夫。这片月华遍照的世间,充满了深情与真挚,千百年来,深深打动着人们的心。今天读来,仍然为之掩卷长思。
关于月亮的诗篇很多,几乎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月光诗篇,有人写下离别,有人写下故乡,有人写下爱情。月光是一个人心上最白的白,思念是一个人心上最重的重。直到今天,我们读到这首《月夜》,仍然能够感受到一种贴肤的亲切,在鄜州,那银色的月光下,铺满了温暖的情意,诗歌的芳香浸润着心灵,仿佛杜甫从未离开。
其实杜甫的一生并不诗意,相反,这是一个失意了一辈子的人。每次想起他,总觉得从异乡到异乡的奔波中,他始终是一副拖儿带女,步履沉重的样子。从来没有我们对于诗人的想象里那份洒脱与轻捷。
李白的诗里,到处有朋友,到处有美酒,到处有宠爱,到处有夸赞。他居无定所,萍踪漂泊,这是诗仙的风度。一篇又一篇的诗歌被世人争相传阅,从市井到宫廷都有关于他的传说,他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丰富的谈资,连皇家也对他充满了兴趣。总之,他卓然出尘,没有丝毫的人间烟火气息。
而杜甫不是,在他的诗歌里,总有放不下的人间拖累。在很多诗篇里都有家人的影子:“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家人是他甜蜜的负担,曾经有佛门友人看到他负累太重,便劝其遁入空门,但他毫不迟疑地答复说,参禅悟法之后,自己钟爱的诗歌可以放下,不再吟咏;一生嗜好的美酒也可以放弃,不再贪杯。但是割舍妻子儿女,却是不可能的。
世间的家庭负累,大都一样,不过有的人会陷入生活的泥淖,逐渐被淹没。可是对于他,诗歌恰似从泥淖中开出的莲花,饱满生动。即使隔了一千多年,仍然能闻到诗歌中的芬芳,那是人间欢乐的情味。
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认为危难时刻理应报效国家,拯救苍生,作为一个儒家知识分子,这是内心的自觉,也是必然的选择。于是,将妻儿老小一家人安顿在鄜州的羌村之后,北上寻找刚刚登基的皇帝。
可是,一切都不是想象中的那样,很快,他就发现自己错付了真心。在新朝廷里虽然谋得一个八品小官,但他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因救援同僚兼友人房琯,与皇上的意见发生龃龉,不懂得官场游戏规则,不会圆融乖巧地讨好,结果很快遭到了冷遇。他是那种笨拙的人,在和这个世界的周旋中,左右都不逢源,很快罢官回家。
谁的青春不曾有过远大的抱负呢?为了当官,青年杜甫蜗居长安十年多,屡次向皇帝献赋,为贵人写诗,这个官来得实在太不容易,可是,很快就丢了。事实上,那些归隐山水的,哪个不曾在名利场中红头热眼地搏过?只是没有赢,杜甫也是。
那么,只有回家。只有家人是不会厌弃失败者的。回家的路途遥远,他向别人借马,人家不给,只好步行。靠着双脚的丈量,走了好长时间才回来。刚一见面,家人惊怪:你怎么还活着?乱世的重逢让人有一种荒诞感,原以为他已经死了。
虽然在陕北居住时间并不长,可是,自从他的双脚踏入陕北,很多事情便有了变化。在避乱岁月,他写下著名的《羌村三首》,记录避乱岁月的艰苦生活,因为他曾路过延安,人们就将他走过的川道命名为杜甫川。从此,陕北便与杜甫有了某种关联,直到今天,提起杜甫我们觉得亲切,因为他来过,他写过。陕北有他的呼吸,他的歌吟,他的脚印。
从对长安繁华世界的热望追逐,到成都浣花溪旁的寄情山水,他似乎一步一步向后退,退至自己的家里,退至自己的内心。既然兼济天下的梦想难以实现,写诗就成了安顿内心的方式。杜甫有诗:语不惊人死不休。在我看来,苦吟的背后是欣然。这种难以为外人道的滋味,隐藏在艰难里面。失意漂泊的一生,是诗歌照亮了他,满足了他,也快乐了他。
每次翻阅杜甫的诗卷,总能体味到他的慈悲,柔软的心肠使他不仅关注家人、朋友,更关注每一个普通人。为他者的痛苦而痛苦,仿佛天下的苦痛都与他有关。那些诗歌,读来令人眼眶发热,喉头发紧。一千多年的大浪淘沙,这个养不活儿女,仕途上处处碰壁的人,他的名字却留下来了,与李白一起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
小小的羌村,因了杜甫的《羌村三首》,它的名字便镶嵌在唐诗里,成为一个诗意的村庄,一个坚硬的存在。每年,总会有一些人,来到这里,追寻他的踪迹,追寻诗人撒播的遗香。而陕北,也因为他,散发着岁月深处的幽幽书香。
范公的秋天
此刻,延安已经是深秋,在暮色苍茫中,寒意渐浓,从脚下直逼心底。总是这样的,秋天总会让人无端惆怅……
一千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天,也是这样一个暮色苍茫时刻,在边城延州,头白如雪的范仲淹缓缓研墨提笔,将对故土亲人的思念凝于笔尖,写下了《渔家傲·秋思》。
一千年后,我坐在教室里,等待着下课。少年时期,每一天都那么漫长,看看窗外,太阳当空,一动不动,远处的祁连山呈现出一派秋意,大雁排云高飞,要到南方过冬。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我们的老师是北京知青,字正腔圆地朗诵那阙《渔家傲·秋思》,念到最后一句,美好的男中音哽咽了一下。
老师也是离家千里,有家不能归,自然格外共情。他说,人生的无奈都在这最后七个字里面:“将军白发征夫泪”,白发是生命 不得不承受的煎熬。可是,一个少年怎么能懂呢?那时候,只盼望着快快长大,离家越远越好,就像大雁,飞得越远好像越有出息。
如今,当我站在人生的秋天,金黄的落叶堆满了心间,忽然明白了他的煎熬。
东汉时期,车骑将军窦宪领兵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于燕然山勒石记功,从此威名远扬,被后世景仰。可是,此时的范仲淹苦守延州,建功立业杳如黄鹤,解甲归田亦遥遥无期,来路茫茫,去路亦茫茫……
只不过,他并没有料到,从延州开始,他的非凡人生才刚刚拉开了序幕……
北宋时期,陕北以北的党项族迅速崛起,1038年,李元昊建立了西夏,自称皇帝,亲自率领十万大军进犯。草原民族异常强悍,延州老百姓惨遭劫掠杀戮。一时边地告急,消息传到开封,朝堂之上议论纷纷,有人主战,有人主和,皇帝举棋不定,太久的和平年代,使人忘记了战争,刀枪入库,马放南山,打仗谈何容易!
此时的范仲淹已经年过半百,俨然进入了人生的秋天,半生宦海沉浮,仕途不顺,要是按照今天干部队伍年轻化的标准,该退二线了。可是,国家有难之际,他临危受命,挺身而出。
总是这样的,在这个国度,在危难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人,像顶梁柱一般,苦苦支撑局面。
范仲淹出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也就是延安的一把手,在边地驻军期间,他加强防御,拒敌于城外,无奈同僚韩琦想法不同,主张主动出击,大举反攻。1041年,宋军在好水川遭到伏击包围,死伤惨烈,一万多官兵阵亡。噩耗传来,延州的亡灵家属哭声震天,韩琦也是掩面痛哭,悔不当初。
延州的防御不断加强的同时,范仲淹也在积极备战,他深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没有精兵强将就没有战胜西夏的可能。他从陕北民间拔擢了大量人才,加强军事训练,很快培养了一支精锐部队,几番较量,西夏兵不敢进犯,一时边塞和平气象重新降临。
世界上的和平都是用实力争取来的,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没有和平。
他不仅懂得军事,更懂得政治。在边境地带,他开办贸易,活跃经济,加强汉人和边地少数民族生意来往,增加了老百姓的财富,融合了彼此之间的感情,大大弱化了民族对立的情绪。甚至在他死后,边地的羌族百姓为他戴孝哭灵,嚎啕涕泣,声闻于天。
三年的坚守之后,范公调任回京,一度官至参知政事,大约相当于宰相。这是他的最高职位,可是在我看来,这并不算他生命的巅峰,因为他所主持的“庆历新政”很快就以失败告终。
延州之后的杭州,应该是他职场生涯的另一个重要节点。
1050年,江浙一带发生大旱,田间颗粒无收,许多老百姓打算外出逃荒。他下令大兴土木修建寺院,举办龙舟赛。当时很多人不理解,纷纷上书弹劾,他解释说,大兴土木是让老百姓找到活路,以工代赈解决吃饭问题。这大概是最早的“大项目拉动”,保证了老百姓就业。至于举办龙舟赛,就是今天的“旅游经济”,促进消费,让富人的钱流向穷人的口袋,而不至于富者越富,穷者越穷。
自古以来,在我国一有饥荒就会有流民,饿殍遍野,骨肉相食,在史书上屡见不鲜。可是,他管理下的江浙一带却没有,“大项目拉动”和“旅游经济”为老百姓找到了饭碗,保住了性命。
有人说“百无一用是书生”,其实,真正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们带兵能打仗,提笔著文章,为官一方则必造福于民。孔子说,君子不器,指的就是范仲淹这样的人。
如今,在延安城里,昔日的延州,处处都有他的痕迹,不经意就会劈面遇见。清凉山上有纪念他的范公祠,很多人远路风尘来看他,恭恭敬敬地献上一炷心香。
宝塔山下有摩崖石刻,向来车流密集,每次堵车在这里,人们都会看到他亲笔书写的三个大字“嘉岭山”,笔体端严雍容,气象不凡。
而当我行走在宽阔的范公路上,早年镌刻于心的《岳阳楼记》便会从记忆深处纷纷涌现,一时觉得心头风烟俱净,秋日的晴空一般澄澈。
《岳阳楼记》奠定了他生命的高峰。
洞庭湖边的岳阳楼上,依旧能看见那368个字被工工整整镌刻在石壁上,天南海北的人,千里迢迢赶来,一字一句吟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每一个人不由自主地念出声来,南腔北调,男女老幼,渐渐默契为齐声朗诵,仿佛回到少年时的课堂上。
三国时期,文学家曹丕曾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于今想来,并非虚妄。那些文章像一粒种子,种在懵懂少年的心田,在漫长的岁月里,将逐渐生根发芽,潜移默化地塑造一个人的精神世界。终将有那么一天,他会突然领悟,一个人的生命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承担着一种责任或者他人的福祉。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这一刻,你会相信伟大的抱负和勇者的担当绝非虚言,高尚的品德和完美的人格是真实的存在。
范公就是这样一个绝对的生命样本。
沈括的石油
你知道吗?中国石油,最早发现于陕北。
这是一个秘密,隐藏在历史的幽微之处。很多人睁大了眼睛,充满了疑问:陕北,应该是民歌和剪纸的陕北,或者是红色革命的陕北,怎么能和黑色的石油扯上关系呢?
两千年前,历史学家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中记载:“上郡高奴县有洧水,肥可燃。”高奴就是延安,肥就是石油,而洧水就是延河。
那时候,石油还没有今天这般昂贵的身价,伴随着河水,默默流淌,没有人把它当宝贝。就是河边汲水的村姑也会厌嫌地躲避,生怕弄脏了花鞋子。那黑乎乎的物质,难闻,还特别难清洗,顶多用来点灯,可是烟气太大,一阵子烟熏火燎,人是黑面孔,屋是黑墙壁,算不得好油,几乎就是无用之物。
在亿万年的光阴里,它藏身于河水与沙石之间,忍受着冷落,就像一个不起眼的孩子,看不出将来会有什么大出息。此时,它连个像样的名字也没有。
在寂寞中,它耐心地等待一个人。
这一等就是千年。
1080年,50岁的沈括风尘仆仆行走在黄土高原上,他将赴任延州一把手。那时,延州是一个边城,而沈括的主要工作就是驻守边防,加强战备。强敌西夏虎视眈眈,要时刻提防它的入侵。
和很多人一样,沈括是个面目复杂的人。具有多重身份——文人、官员、科学家。
首先是个文人,写过一些诗文,但后人知之甚少,作为文人的沈括,因为嫉妒,曾经陷害过苏东坡而广受诟病,许多人鄙视他的品德,而不愿意与之交往。作为文人的沈括几乎不值一提。他还是官员,可历史上官员太多了,用陕北话说,一扫一簸箕。官员最大的特点就是没特点,都是一张大众脸,就像大街上那些中年男子,脸上写满了复杂的心事,额头上的每一条纹路都指向一段纠结,你常常会认错人,不是眼力不好,只是他们太相似了。总之,在官员堆里,你无法找到沈括,正如沙漠里无法看见一粒沙子。
真正使后世知道沈括的,是他的最后一个身份——科学家,正是这个身份,使他获得了历史的尊重。事情总是这么奇怪,他的官位、权力没有人能记得,倒是一个业余爱好,使他留名千古。
作为科学家,他精通天文、地理、算学、物理、化学,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全才,是文艺复兴时期达芬奇一样的存在。英国学者李约瑟称颂他是“中国科学史上最卓越的人物。”
延河里流淌的无用之物,一直等待的就是他。
人与人之间有一种神奇的感应叫做缘分,其实,在万物之间也存在着缘分。他和石油之间,就有一种深刻的缘分。当他的足迹到达陕北,一些事情就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一直影响到今天。
我常常猜想,或许是某天,当他读到古书里“高奴有洧水,肥可燃。”这句话,心里觉得奇怪,不是人人都讲水火不容吗?怎么书里面说火燃于水上呢?难道洧水有什么特殊之处?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心里装满了好奇,某一天来到了洧水边亲自验看。
繁忙的政务之余,他亲自做实验。在《梦溪笔谈》里,他详尽地叙述了发现石油的经过,并用石油制作石墨,用来代替写字的墨汁。即使今天读起来,我们依然能感觉到那份蓬勃跳动的好奇心以及发现大自然奥秘的喜悦。
在古代,科学是旁门左道,是奇技淫巧。一个人把心思放在科学研究上,无疑是个另类,做另类是需要勇气的,需要强大的内心力量。只有这样,才敢于去追随自己的心,做想做的事。沈括无疑是勇敢的,这份勇敢是拿智慧垫底,给后世带来了泽惠千年的好运气。
他发现了石油,命名了石油,并预言了石油。他说:“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对石油的神奇的预言,今天早已证实。李约瑟说:“《梦溪笔谈》是中国科技史的里程碑”。而陕北进入了《梦溪笔谈》,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公众的视野,研究石油,无法绕开“陕北”这两个字,中国石油的历史将从这里启程。
如今,当我站在高高的山顶瞭望,看见红色的抽油机永不疲倦地向大地母亲叩首,感觉脚下那来自大地深处石油的脉动,就不由地想到了沈括,想到了他披星戴月赶奔赴延州。也许,此番前来,只是为了遇见石油。
感恩沈括,他发现了石油,赋予了这黑色物质一个好听的名字,我再也想不出,还有哪一个名字更贴切、更动听。你听,石油。多么雅致,多么生动,多么抑扬顿挫。
感恩石油,这黑色的液体金子,至今还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彻底改变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在陕北,石油工业的迅猛发展,让黄土高原上世世代代生活的人们摆脱了贫穷的命运。
而沈括,因为石油,获得了历史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