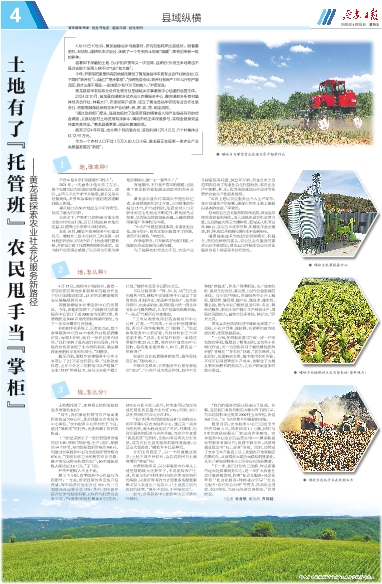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4月25日
土地有了“托管班”农民甩手当“掌柜”
 ● 崾崄乡马蹄掌村正在进行集中锄草作业
● 崾崄乡马蹄掌村正在进行集中锄草作业  ● 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
● 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  ● 崾崄乡白城桥村玉米长势良好(资料照片)
● 崾崄乡白城桥村玉米长势良好(资料照片)  ● 崾崄乡农机手正在收割玉米
● 崾崄乡农机手正在收割玉米  崾崄乡鲁家塬村“千亩方”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
崾崄乡鲁家塬村“千亩方”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 4月14日10时许,黄龙县崾崄乡马蹄掌村,农机的轰鸣声此起彼伏。随着撒肥机、犁地机、旋耕机依次驶过,休眠了一个冬天的土地被“唤醒”,即将迎来新一轮的耕种。
看着脚下深翻的土地,59岁的尹贵军头一次觉得,自家的60亩玉米地再也不是过去那个压得人喘不过气的“老大难”。
今年,尹贵军把家里所有的地都托管给了黄龙县裕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联合社”),当起了“甩手掌柜”。“按照托管协议,联合社有亩产750公斤的产量兜底,我什么都不用管,一亩地至少有600元的收入。”尹贵军说。
黄龙县裕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组建的运营主体。
2024年10月,黄龙县在崾崄乡试点成立农事服务中心,整合崾崄乡所有村集体经济合作社、种粮大户、农资经营户资源,成立了黄龙县裕华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将服务触角延伸到玉米产业的耕、种、管、收、售、销全流程。
“通过政府部门牵头,既有效把控了政策资源的精准投入和产业链各环节的综合调度,又推动各村土地资源有序集中,调动市场主体深度参与,实现全链条效益共建共营共享。”黄龙县委常委、副县长曹增俊说。
截至2024年年底,成立两个月的联合社,实现利润126.1万元,6个村集体分红12.61万元。
作为一个农村人口不过1.8万人的人口小县,黄龙县正在摸索一条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
1 地,谁来种?
尹贵军是乡亲们眼里的“可怜人”。
2021年,一次意外让他失去了左手,整个左臂也因为后遗症变得虚弱无力。彼时,正值儿子大学求学关键期,妻子又身有轻微残疾,尹贵军原本就不宽裕的家庭瞬间陷入困境。
赖以糊口的60亩地既是全家的希望,也成了最大的负担。
无奈之下,尹贵军只好把60亩地全都交给同村邻居打理,自己只保留30亩地的收益,以便腾出手来养牛补贴家用。
去年10月,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建成投用。崾崄乡二级主任科员王向龙第一时间找到尹贵军,向他介绍了土地全程托管套餐,并帮他申请了托管费兜底帮扶政策。如今的尹贵军满心感激:“以后再也不用为种地的事操心,能一心一意养牛了。”
有地难种,不只是尹贵军的难题,也是整个黄龙县农业发展必须面对的当务之急。
黄龙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健告诉记者,全县耕地面积27.2万亩,人均耕地面积超过15亩,但与此同时,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程度不断提升,耕地候鸟式经营、低价转包经营现象普遍,大量的耕地面临着广种薄收的困境。
“小农户分散经营成本高、专业化程度低,留守农户、候鸟式农民既管不了耕地,也管不好耕地。”李健说。
在李健看来,只有解决好地的问题,才能解决农业发展的出路问题。
为了破解农村劳动力不足、农业产业化程度低等问题,2022年开始,黄龙县在全县范围内启动了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将农业生产中的耕、种、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业环节托管给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
“本质上是以农业服务业介入生产环节,弥补前端生产的短板,确保农民在土地上能获得基本的收益。”李健说。
趁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持续拓展,黄龙县持续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大成熟先进农机应用力度,先后购置大型玉米播种机、植保无人机等设备106台,实现玉米化学控草、机械化作业全覆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耕作水平达到95%。
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尝到规模化、机械化、集约化种粮的甜头,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黄龙县也开始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上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2 地,怎么种?
4月15日,崾崄乡白城桥村,看着一袋袋化肥在犁地机和旋耕机的联合作业下均匀地撒进地里,43岁的刘鹏紧皱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
刘鹏是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的托管员。今年,在他的协调下,白城桥村与农事服务中心签订了近3000亩的托管订单,他要确保这3000亩地按照标准深耕到位,为下一步玉米播种打好基础。
在他的手机系统上,记者注意到,整个农事服务中心的44台农机作业轨迹清晰可见,每隔5分钟,就有一张作业照片回传。“我们采购了最先进的农机设备,并为每台农机都装配了北斗导航系统,确保耕种流程的科学化和标准化。”刘鹏说。
截至目前,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在全乡签订了2.2万亩全托管订单。“这也就意味着,全乡三分之二的耕地可以严格推广玉米‘5335’种植技术,执行玉米单产提升计划。”崾崄乡党委书记薛兴文说。
与以往提供单一“耕、种、防、收”的社会化服务不同,崾崄乡农事服务中心建立了农资供应、机械作业、新品种实验推广、技术指导培训、病虫害防治、收割销售六统一的全环节社会化服务模式,从生产前端到销售后端,“一站式”代理所有种地难题。
“玉米从地里收割后就直接拉回中心过秤、付款,一气呵成,十来分钟就能拿到钱,再也不用等收购商上门收购了。”说起农事服务中心的好处,伍姓村村民王占华滔滔不绝:“过去,玉米秸秆回收一亩地还得额外掏25元工费,现在秸秆直接由中心回收,每亩地还能再收入10元,简直是一举两得!”
农业社会化托管服务的效果,最终要体现在农户的收益上。
在薛兴文看来,农事服务中心是专家级的“农民”。“小农户基本都会种地,其中不乏种地‘老把式’,但生产管理粗放、生产效率较低、组织化程度低,难以跟上现代农业发展的步伐。与小农户相比,农事服务中心分工精细,懂经营、懂管理、懂产业、懂技术、懂市场、懂金融,能为小农户提供更加科学、专业、精细的服务,帮助小农户提升生产经营水平、增强抗风险能力,最终实现多种地、种好地。”薛兴文说。
黄龙县农经站站长刘宇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小农户自种、流转种、托管种的亩均收益比较,托管效益最高。
“一方面,托管服务通过打破一家一户承包地的界限,既增加了耕地面积,又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另一方面也有利于避免耕地流转后的‘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刘宇峰说,与此同时,批量购买农资、集中使用农机作业,不仅可以明显降低生产成本,也解放了大批从事田间耕作的劳动力,让农户拓展更多的就业渠道。
3 钱,怎么分?
土地都托管了,如何把土地增值效益更多地留给农民?
“首先,我们保证托管的农户每亩地保底收益750公斤,其余风险由农事服务中心承担。”农事服务中心理事长王飞说,通过“保底式”的托管,优先保障了农民的收益。
王飞给记者展示了一张托管服务价格的对比表:按照市场价格,生产、收贮、销售的14个环节,每亩地托管的价格为760元,但通过农事服务中心的全流程托管价格为678元。“按照去年玉米销售的市价来看,像尹贵军这种全托管的农户,60亩地保底收入能达到3.6万元。”王飞说。
尹贵军的收入不止于此。
据王飞介绍,农事服务中心收益分为四部分:一方面,按照政策性固定资产投资量,每年给各村固定分红10%;另一方面联合社运营分红75%(其中:25%留存联合社作为发展积累,13%作为托管员业务分红,7%激励奖励村集体和托管员,55%由分社分红);此外,村集体再以每年完成托管任务总量占比分红10%;同时,农户以托管面积的占比分红5%。
“我们将所有的增值效益和节省的成本都牢牢集中在农事服务中心,通过这一利益分配机制,最大程度实现了农民、村集体、社会化服务组织多方合作共赢,而农户在享受‘保底托管’的同时,还能再享受两次分红收益,成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最终受益者,也是最大受益者。”崾崄乡乡长景烽说。
分红比例确定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土地不用农民耕种,会造成农民与土地纽带的“断裂”吗?
在曹增俊看来,以农事服务中心牵头土地托管的最大优势在于,不用流转农户土地,而是与农户共同承担自然灾害风险和市场风险,以政府背书的方式使更多资源要素集中投入农业生产运营中,让土地真正成为农民的依靠,“离乡不丢地、不种保收益”。
如今,农事服务中心的影响力正不断向外辐射。
“我们的服务范围已经走出了县城。你瞧,这是我们业务员刚在内蒙古签下的订单,为当地饲料企业提供2000吨玉米籽粒,价值360万元。”王飞兴奋地介绍最新的成绩。
截至目前,农事服务中心已完成玉米销售2248万元,秸秆回收1.1万捆,同时与5家农资供应源头厂家达成合作意向。农事服务中心设立的运营公司——黄龙联盈农事服务有限公司,组建不到半年,就顺利通过延安市“五上企业”审核。同时,还带动了全乡玉米产业迈上从土地到农户全面抱团的集约化、从前端到末端全面联结的链条化、从生产到经营精准分工的专业化的新赛道。
“下一步,我们计划在三岔镇、界头庙镇再建两处农事服务中心,进一步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覆盖面,探索‘社会化服务+社会化养老’‘社会化服务+转移就业引导’‘社会化服务+农村综合治理’等模式,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县域经济发展探路。”曹增俊说。 (记者 杜音樵 通讯员 白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