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
老张的艺术细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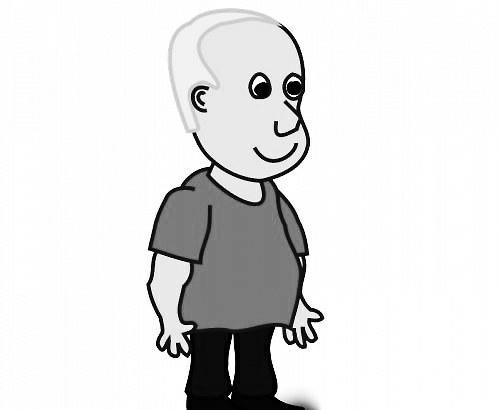 第一次见老张,好像在食堂。一个糟老头的样子,别人打饭都嫌少,只有他一个劲说,够了够了,不要超过这!然后手指在饭盒里某个位置。因为不熟,就没有在意,以为是退休职工或者哪家家属。
第一次见老张,好像在食堂。一个糟老头的样子,别人打饭都嫌少,只有他一个劲说,够了够了,不要超过这!然后手指在饭盒里某个位置。因为不熟,就没有在意,以为是退休职工或者哪家家属。 等到我第一次去参加公司乐队训练的时候,教练站在白板前讲授乐理,正是这个老头。有点小小意外,我一直以为搞音乐的人形象好气质佳嗓音甜美。老头讲乐理不很正经,自己写一段简谱,磨磨唧唧挨个叫人唱谱,学员唱得五花八门,他点评的,大家哈哈大笑。
一个女学员看着简谱恍然大悟地说:“东方红!”
“我的妈呀!”老头夸张地回应,此后不管这个女学员唱什么谱他都续唱几句《东方红》。
正是老头的随和幽默,他的饭桌对面总有人作陪,走在路上几乎每个人都打招呼。后来我就和他熟了。
老头姓张,有一双胞胎兄弟,由于早出生一点,人称老大。他很有艺术细胞。有一天,送我两幅字,我说无功不受禄。老张说没事,他弟弟写的,喜欢的话还有。双胞胎真的很神奇呢,一个搞音乐、一个写字,看来艺术细胞真的是天生的。
老张的特长是吹萨克斯。他经常说,把人吹哭了才能吹好。训练休息时间,他也拿起来吹一曲,我们是没有哭,他的眼圈却红了,真是一曲《枉凝眉》,两眼泛红圈。当然,老张的艺术细胞远不止于音乐。
吃完饭在路上碰见一些景观树,树枝被修剪得七扭八拐。这条路我走了多少遭,从来没有注意到这些。唯有老张路过一次欣赏一次,欣赏一次赞一次,那描述、那比划,恨不得挖出来栽回家。老张把手机打开,给我炫一炫他收藏加工的树根。
翻到一张图片,问我像什么。我说像树根啊。
“鳄——鱼”!
又看一张图片,直立一截树根,顶着一颗小圆球。我突然灵光一闪,海豚?
“对啦”!
其实,要不是那颗小圆球,它还是像树根。他把别人送他的锯得只剩下三五枝丫的下脚料视若珍宝,号称崖柏,准备钉在墙上做衣架。他胸前挂着一个过去练武人举重用的石锁一样的小硬木,自称穿线的孔是亲自用锥子手工钻出的,钻了一天。
没办法,有艺术细胞的人,不仅手里有、眼里有,而且浑身上下都有。
要说老张退休几年了,有养老金吃喝不愁,还要出来靠才艺吃饭。用他的话说,本应该抱孙子了,无奈儿子不听话,括弧没结婚。这真是把家里老头老太太的命不当回事的节奏啊。好在最近儿子又是买车、又是买房,可能快要结婚,老张也有出来发挥余热的心劲。
老张年轻时在一家国有企业上班,嫌工资太低,想方设法离开单位后自学音乐谋生,要不然说他有艺术细胞呢。
老张的记性太好了。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发生了什么事,谁谁谁先说什么话,谁谁谁再说什么话,他都讲得和昨天发生的一样。他讲过参加萨克斯考级的事情,主考官是萨克斯领域的名家大腕某某某,考完试上厕所正好偶遇,名家对他点点头说小伙子吹得不错,结果一出来国家二级!
国家二级是什么水平,我没有作进一步的了解,但看他的神色,钦佩之心油然而生。
他也讲过年轻时组织乐队在舞厅谋生,他吹萨克斯,一个架子鼓手兼男歌手,一个女歌手。一晚上的报酬最开始是两毛钱,某年涨到五毛钱,某年涨到一块二,老张清楚得像翻账本一样。正是有了这样的经历和实力,他才能在我们这里担任业余乐队教练。
老张的音乐路程为什么从舞厅直接跳到乐团呢,原来这中间他给一家私企老板开了几年车。最让老张回味无穷的是开气囊减震的林肯车,坐着和坐轿子一样舒服。
说来你们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老张还当过几年游泳教练呢。我都有点怀疑他不只有艺术细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