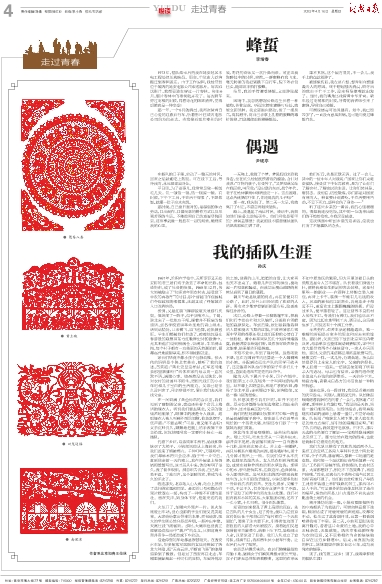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4月16日
我的插队生涯
1967年,堆积在学校中、无所事事又无处安排的老三届们终于敛去了革命的光彩,混迹街市,成了社会的负担。1968年12月,伟大领袖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号召,那个曾被用作包围城市夺取政权的根据地,此刻又成了纾解城市人口的消纳场。
按例,又是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地游行庆贺。但热闹了一阵子,似乎反响不大。于是,陕北来了一批地方干部,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到各学校宣讲革命圣地的青山绿水。话到动情处,口沫横飞,眉飞色舞,还热泪盈眶。学生们都被他们打动了,痴痴地沉浸在春游般的联想和东方红歌舞史诗的激情中。尤其听他们说到粮满仓、谷满垛、牛羊满山岗,每个村子都有一方美丽的天然湖泊时,便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恨不得拔脚就走。
家长们毕竟不像小孩子这般幼稚。张大伟的妈妈是个陕北老革命,她听了我的叙述,苦笑道:“陕北要是这样好,红军还可能去那里落脚吗?”病休在家的母亲则一直沉默不语,满腹心事。她虽然没去过陕北,但对农村的贫困并不陌生,更担忧我们的小小年纪和几乎空白的生活能力。父亲已经很久没回家了,母亲举棋不定,便让我们去天津找父亲。
在一间刷满了各色标语的会议室,我们见到了瘦削的父亲,旁边还坐着个会说上海话的绿衣人。听说我们要去陕北,父亲的脸痛苦地绷紧了,眼神中的凄楚令人战栗。趁那绿衣人被人叫到外面的间隙,他急急摆手,低声道:“不要去啊!”可是,谁又能不去呢?父亲沉吟良久,默默地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沉沉地嘱咐我一定要和小妹在一起插队。
凭着下乡证,母亲倾家中所有,给我和妹妹买了大箱子。小姨闻讯也从上海赶来,给我们送来了棉被棉衣。千种叮咛,万般吩咐,我们却麻木得只会应承,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外屋桌上给奶奶和爸爸写信,这才悲从中来,饮泣哽咽了很久,流了很多眼泪。潜意识告诉我,自己将一去不返。于我而言,这个温暖的家,将成为永久的怀念了。
临走那天,北京站人山人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和同学。豪迈的口号和撕心的哭泣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悲壮。爸在天津,妈身体不好,是姐来送的我们。
火车开了,车厢内外哭声一片。但火车刚驶出车站,没心没肺的学生们便又说笑起来。大家纷纷拿出带来的水果、面包请客,胆大的学生则公然分派起香烟,一派冲出牢笼、天高任我飞的雀跃。那时,大概谁也没真正理解最高指示中“落户”的含义,只把这离乡背井看作一场郊游或下乡劳动。
沿途停靠的车站都是锣鼓喧天。在西安火车站,很多解放军医院的女兵还舞起了陕北大秧歌,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浪漫渲染到了极致。但是过了西安再往北走,车厢里便氤氲起一种可怕的压抑。车窗外荒凉的土地,贫瘠的山川,皑皑的白雪,让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随着几声压抑的抽泣,搅动起一片叹息和躁动。而我却从漫山遍野的荆棘丛看到了夏日的葳蕤。
铜川车站是轨道的终点,再往前便只有公路了。此时,站台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男女老少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袄,脸蛋冻得红扑扑的。
次日,公路上停着一长溜敞篷军车,把我们和行李按公社和大队编组,分送到白雪皑皑的高原深处。车到黄陵,依旧是载歌载舞的人群和漫天飞舞的红旗,但黄帝陵那片雪原中罕见的苍翠还是让我们压抑的心情有了一丝轻松。看小妹和同队的几个知青情绪落寞,我便讲故事给她们听,虽然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结果却依旧是落寞。
不知不觉中,车到了隆坊镇。虽然破败不堪,但在方圆百里内还算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小镇。分配到边远生产队的同学可就苦了,还要跟着各队拉行李的架子车步行几十公里,直到走进风雪茫茫的丘峦中。
隆坊大队下属五个小队,四个在城中。我们的第五小队在城外一个叫南场的塬湾里。站在塬上四野望去,都是广袤的农田,像极了华北平原;走到塬边下瞰,深沟险壑,又是一番山区的景象。
队长憨笑着引我们回村,却并不见村落。原来农舍都散布在塬边绝壁上掏出来的土窑中,这才是真正的穴居。
我们的驻地被临时安排在村中唯一的也是最显赫的厦子房中。房东是儿子在县里当局长的一个孤老太婆,村里还专门派了一个婆姨为我们做饭。
陕北的生活是艰难的。最苦恼的是缺水。塬上无河,吃水全凭从一口老井取水。那井深不见底,我曾抛石测深——自由落体十几秒,算来竟达30余丈。井上支一架辘轳,两只吊桶系在粗绳的两端,摇动辘轳柄,须十几分钟才能吊上一桶。农民们似乎从不洗澡,也鲜见洗脸洗头。女人洗衣则到沟底溪边,或聚在被称作涝池的雨水塘边洗。那塘中的水,驴马猪狗共享,边饮边尿,色泽黄绿,令人匪夷所思。这吊水担水的活自然是我和桂生的,女生们则负责做饭,小妹还要多负担一份给我洗衣的劳苦。男生吃得多,又懒于干活,于是不久,很多知青点便产生了矛盾,终于引发了知青中的男女生分灶潮。我们村因有我和小妹的关系,大家抱团取暖,还养了一头小猪,十几只鸡。很令别队羡慕。
知青的到来搅乱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先是四队的几个女生,见了涝池,便以为是到京宣传的公社干部胡诌的“每村都有一个天然湖泊”,便换了泳衣要下水,引得涝池边围了密匝匝的人群看大姑娘脱衣。接着她们又把烟苗偷来当菠菜吃,结果上吐下泻,险些闹出人命,以至惊动了县委。我们大队成立了宣传队,排演节目,我和贵生拉小提琴伴奏。让农民们大开了眼界。
农活是枯燥乏味的。农民们懒懒散散地荷锄下地,婆姨女子们嬉笑着搬弄家长里短,汉子们肆无忌惮地唱着酸曲。这里的农事远不如中原地区的繁重,但大田里顶着日头的煎熬还是令人苦不堪言。队长看我们身强力壮,便将我和桂生派到粮库去装粮。这是村里唯一的副业——在磅秤上将粮食装入麻包,再背上卡车,装满一车能有几毛钱的收入。沉重的麻包初压到肩头,我竟连步子都迈不开,更遑论走上颤颤巍巍的跳板。但没过多久,便举重若轻了。这让营养不良的村人惊叹不已,夸我们有神力,我们也乐此不疲。因为比起在地里耗工夫、晒日头,这活痛快多了,何况还有十个满工分挣。
辛苦劳作、艰苦生活还都能适应。唯一难解的苦闷是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惶恐。那时候,父亲已经下放到北京军区内蒙兵团,母亲单位也整体调动到嘉峪关,家中只有大姐带着两个小妹妹留守,一家人分居四地。那时,父亲的来信都是用拓蓝纸誊写的,就像文件一样,一式几份,分寄各地。抬头自然是罗列上全家人的名字。父亲的信很长,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一信读罢便知晓了所有亲人的近况。母亲也有信来,亲情的纽带便全靠这八分钱的邮票维系。一天劳作下来,精疲力竭,读着来自各方的书信也是一种精神抚慰。
说来也怪,有一段时间,我总是看着西南的天空发亮。问别人,竟都说无异。队长眯起眼睛循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恍然道:“对着呢,那崖畔上有盏灯哩。”我说的是天色,岂是一盏灯能照亮的。但经他指点,我果真发现沟对面的崖畔上悬着一盏灯,不觉好奇起来。队长说:“咱陕北人掉下崖,家人就在失足的地方点盏灯,好引他的魂魄回家哩。”听了队长的话,我顿觉汗毛凛凛。但不久,那片天边的亮色便有了解证——宝鸡铁路局到陕北来招工了。那方位恰在隆坊的西南,也就是我眼中泛着亮色的地方。
我们大队只推荐了我和苏凤霞两个人。来招工的宝鸡工务段人事科科长是个陕北老红军,个子不高,慈眉善目,操着一口地道的延安腔。他和每一个面试的知青都重复着一句话:“工务段可是砸洋镐、修铁路的,比农村还累。大家都想好了,别吃不下苦哭鼻子,再退回来哦。”后来,还真有几个去梅七线当过民工的知青被吓退了。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养路工就是在铁道上养护铁路的苦工,那活可不是人干的。”可是更多的知青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不肯失去这跳出黄土地的机会。
离开隆坊的前一晚,小妹和夏阳把所有的小鸡都杀了为我送行。可惜肉块直接下油锅,顿时结成了死硬死硬的肉疙瘩,咬都咬不动。桂生买了盒香烟开戒,这第一根香烟呛得我咳了半宿。第二天,小妹和夏阳送我离开隆坊,看着这片金黄的土地,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无限感慨。既庆幸能逃脱终身为农的厄运,又不忍将相依为命的妹妹独自留在这穷乡僻壤中。后来,果真因为我的招工,妹妹羁留在陕北长达七年,成为我愧疚的憾事。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别了,我魂牵梦绕的插队生涯!
按例,又是红旗飞舞锣鼓喧天地游行庆贺。但热闹了一阵子,似乎反响不大。于是,陕北来了一批地方干部,操着并不标准的普通话,到各学校宣讲革命圣地的青山绿水。话到动情处,口沫横飞,眉飞色舞,还热泪盈眶。学生们都被他们打动了,痴痴地沉浸在春游般的联想和东方红歌舞史诗的激情中。尤其听他们说到粮满仓、谷满垛、牛羊满山岗,每个村子都有一方美丽的天然湖泊时,便都高兴地鼓起掌来,恨不得拔脚就走。
家长们毕竟不像小孩子这般幼稚。张大伟的妈妈是个陕北老革命,她听了我的叙述,苦笑道:“陕北要是这样好,红军还可能去那里落脚吗?”病休在家的母亲则一直沉默不语,满腹心事。她虽然没去过陕北,但对农村的贫困并不陌生,更担忧我们的小小年纪和几乎空白的生活能力。父亲已经很久没回家了,母亲举棋不定,便让我们去天津找父亲。
在一间刷满了各色标语的会议室,我们见到了瘦削的父亲,旁边还坐着个会说上海话的绿衣人。听说我们要去陕北,父亲的脸痛苦地绷紧了,眼神中的凄楚令人战栗。趁那绿衣人被人叫到外面的间隙,他急急摆手,低声道:“不要去啊!”可是,谁又能不去呢?父亲沉吟良久,默默地把腕上的手表摘下来交给我,沉沉地嘱咐我一定要和小妹在一起插队。
凭着下乡证,母亲倾家中所有,给我和妹妹买了大箱子。小姨闻讯也从上海赶来,给我们送来了棉被棉衣。千种叮咛,万般吩咐,我们却麻木得只会应承,脑子里一片空白。直到临走前一天的晚上,我在外屋桌上给奶奶和爸爸写信,这才悲从中来,饮泣哽咽了很久,流了很多眼泪。潜意识告诉我,自己将一去不返。于我而言,这个温暖的家,将成为永久的怀念了。
临走那天,北京站人山人海,站台上挤满了送行的家属和同学。豪迈的口号和撕心的哭泣搅混在一起,构成了一种极不和谐的悲壮。爸在天津,妈身体不好,是姐来送的我们。
火车开了,车厢内外哭声一片。但火车刚驶出车站,没心没肺的学生们便又说笑起来。大家纷纷拿出带来的水果、面包请客,胆大的学生则公然分派起香烟,一派冲出牢笼、天高任我飞的雀跃。那时,大概谁也没真正理解最高指示中“落户”的含义,只把这离乡背井看作一场郊游或下乡劳动。
沿途停靠的车站都是锣鼓喧天。在西安火车站,很多解放军医院的女兵还舞起了陕北大秧歌,把“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浪漫渲染到了极致。但是过了西安再往北走,车厢里便氤氲起一种可怕的压抑。车窗外荒凉的土地,贫瘠的山川,皑皑的白雪,让大家再也笑不出来了。随着几声压抑的抽泣,搅动起一片叹息和躁动。而我却从漫山遍野的荆棘丛看到了夏日的葳蕤。
铜川车站是轨道的终点,再往前便只有公路了。此时,站台上已经站满了欢迎的人群。男女老少都穿着崭新的蓝布袄,脸蛋冻得红扑扑的。
次日,公路上停着一长溜敞篷军车,把我们和行李按公社和大队编组,分送到白雪皑皑的高原深处。车到黄陵,依旧是载歌载舞的人群和漫天飞舞的红旗,但黄帝陵那片雪原中罕见的苍翠还是让我们压抑的心情有了一丝轻松。看小妹和同队的几个知青情绪落寞,我便讲故事给她们听,虽然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结果却依旧是落寞。
不知不觉中,车到了隆坊镇。虽然破败不堪,但在方圆百里内还算是一个人烟稠密的小镇。分配到边远生产队的同学可就苦了,还要跟着各队拉行李的架子车步行几十公里,直到走进风雪茫茫的丘峦中。
隆坊大队下属五个小队,四个在城中。我们的第五小队在城外一个叫南场的塬湾里。站在塬上四野望去,都是广袤的农田,像极了华北平原;走到塬边下瞰,深沟险壑,又是一番山区的景象。
队长憨笑着引我们回村,却并不见村落。原来农舍都散布在塬边绝壁上掏出来的土窑中,这才是真正的穴居。
我们的驻地被临时安排在村中唯一的也是最显赫的厦子房中。房东是儿子在县里当局长的一个孤老太婆,村里还专门派了一个婆姨为我们做饭。
陕北的生活是艰难的。最苦恼的是缺水。塬上无河,吃水全凭从一口老井取水。那井深不见底,我曾抛石测深——自由落体十几秒,算来竟达30余丈。井上支一架辘轳,两只吊桶系在粗绳的两端,摇动辘轳柄,须十几分钟才能吊上一桶。农民们似乎从不洗澡,也鲜见洗脸洗头。女人洗衣则到沟底溪边,或聚在被称作涝池的雨水塘边洗。那塘中的水,驴马猪狗共享,边饮边尿,色泽黄绿,令人匪夷所思。这吊水担水的活自然是我和桂生的,女生们则负责做饭,小妹还要多负担一份给我洗衣的劳苦。男生吃得多,又懒于干活,于是不久,很多知青点便产生了矛盾,终于引发了知青中的男女生分灶潮。我们村因有我和小妹的关系,大家抱团取暖,还养了一头小猪,十几只鸡。很令别队羡慕。
知青的到来搅乱了黄土高原的沉寂。先是四队的几个女生,见了涝池,便以为是到京宣传的公社干部胡诌的“每村都有一个天然湖泊”,便换了泳衣要下水,引得涝池边围了密匝匝的人群看大姑娘脱衣。接着她们又把烟苗偷来当菠菜吃,结果上吐下泻,险些闹出人命,以至惊动了县委。我们大队成立了宣传队,排演节目,我和贵生拉小提琴伴奏。让农民们大开了眼界。
农活是枯燥乏味的。农民们懒懒散散地荷锄下地,婆姨女子们嬉笑着搬弄家长里短,汉子们肆无忌惮地唱着酸曲。这里的农事远不如中原地区的繁重,但大田里顶着日头的煎熬还是令人苦不堪言。队长看我们身强力壮,便将我和桂生派到粮库去装粮。这是村里唯一的副业——在磅秤上将粮食装入麻包,再背上卡车,装满一车能有几毛钱的收入。沉重的麻包初压到肩头,我竟连步子都迈不开,更遑论走上颤颤巍巍的跳板。但没过多久,便举重若轻了。这让营养不良的村人惊叹不已,夸我们有神力,我们也乐此不疲。因为比起在地里耗工夫、晒日头,这活痛快多了,何况还有十个满工分挣。
辛苦劳作、艰苦生活还都能适应。唯一难解的苦闷是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未来的惶恐。那时候,父亲已经下放到北京军区内蒙兵团,母亲单位也整体调动到嘉峪关,家中只有大姐带着两个小妹妹留守,一家人分居四地。那时,父亲的来信都是用拓蓝纸誊写的,就像文件一样,一式几份,分寄各地。抬头自然是罗列上全家人的名字。父亲的信很长,事无巨细一一道来,一信读罢便知晓了所有亲人的近况。母亲也有信来,亲情的纽带便全靠这八分钱的邮票维系。一天劳作下来,精疲力竭,读着来自各方的书信也是一种精神抚慰。
说来也怪,有一段时间,我总是看着西南的天空发亮。问别人,竟都说无异。队长眯起眼睛循着我指的方向看了一会儿,恍然道:“对着呢,那崖畔上有盏灯哩。”我说的是天色,岂是一盏灯能照亮的。但经他指点,我果真发现沟对面的崖畔上悬着一盏灯,不觉好奇起来。队长说:“咱陕北人掉下崖,家人就在失足的地方点盏灯,好引他的魂魄回家哩。”听了队长的话,我顿觉汗毛凛凛。但不久,那片天边的亮色便有了解证——宝鸡铁路局到陕北来招工了。那方位恰在隆坊的西南,也就是我眼中泛着亮色的地方。
我们大队只推荐了我和苏凤霞两个人。来招工的宝鸡工务段人事科科长是个陕北老红军,个子不高,慈眉善目,操着一口地道的延安腔。他和每一个面试的知青都重复着一句话:“工务段可是砸洋镐、修铁路的,比农村还累。大家都想好了,别吃不下苦哭鼻子,再退回来哦。”后来,还真有几个去梅七线当过民工的知青被吓退了。他们危言耸听地说:“养路工就是在铁道上养护铁路的苦工,那活可不是人干的。”可是更多的知青像是抓住了救命的稻草,纵然前面是刀山火海也不肯失去这跳出黄土地的机会。
离开隆坊的前一晚,小妹和夏阳把所有的小鸡都杀了为我送行。可惜肉块直接下油锅,顿时结成了死硬死硬的肉疙瘩,咬都咬不动。桂生买了盒香烟开戒,这第一根香烟呛得我咳了半宿。第二天,小妹和夏阳送我离开隆坊,看着这片金黄的土地,我的心中五味杂陈,无限感慨。既庆幸能逃脱终身为农的厄运,又不忍将相依为命的妹妹独自留在这穷乡僻壤中。后来,果真因为我的招工,妹妹羁留在陕北长达七年,成为我愧疚的憾事。
别了,我的第二故乡!别了,我魂牵梦绕的插队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