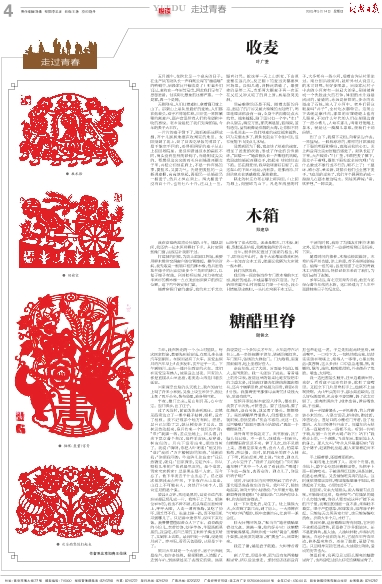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5月14日
收麦
五月端午,在陕北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在生产队的段队长一声响彻云霄的“搂造喽”的呐喊中,后段家河开镰收麦了!听老乡们说过,麦收在一年里苦最重,因此我们早有了思想准备。但实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一个是累,再一个是渴。
天刚刚亮,人们扛着麦担、拿着镰刀就上山了。那架山上是队里最好的麦地,人们都在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忙着,只听见一阵阵唰唰的割麦声,那声音里带着人们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老乡说是托了我们知青的福,今年的麦子大丰收。
一片片的麦子倒下了,随后被迅速捆成捆,齐个儿展展地摆在收割完的地里。太阳照到了坡上,到了回去吃早饭的时辰了,是不能空手回的,还得把捆好的麦子从山上担回场院里。麦担和普通担水的扁担不同,两头没有挂桶的铁钩子,而是削成尖尖的。要想把这尖尖的两头分别插进两捆麦子里,再把它们担在肩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技术,又要力气。先是把麦担的一头插进麦捆,高高地举起,再把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然后才担在肩上。两大捆麦子没有百十斤,也有七八十斤,往肩上一压,腿直打晃。就这样一天上山割麦、下山担麦要往返几次,反正割下的麦当天都要担回场里。没担几趟,肩膀就磨破了。最要命的是第二天,当那两大捆麦子再一次压在又红又肿又破了的肩上时,真是欲哭无泪。
但最难熬的还是干渴。随着太阳的升高,湿透了的汗衫又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干,嘴里连唾沫都没有一滴,全身干枯得像是点火就着。越来越渴,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水!”抬头望去,晴空万里,那天真是蓝,蓝得深,蓝得透亮,蓝得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让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们割麦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麦捆太多了,段队长就会下令往回送,这样就能下山找点儿水喝。
没想到因为干渴,竟加快了割麦的速度、增加了送麦的次数,形成了作业的良性循环。“回喽……”随着段队长一声嘶哑的呐喊,我迅速地插起两捆麦子,担起来飞快地往山下跑。还在割麦时,我早就琢磨好目标了,在这架山的下面不远处,就有泉。是那清凉、甘甜的泉水在诱惑着我、驱使着我。
陕北的村庄分布在塬上和沟里,山上即为塬上,沟里即为山下。凡是在沟里的村子,大多都有一条小河,顺着山沟从村里流过。刚分到后段家河,就听外村人说这儿的水可好哩,有好多眼泉。后段家河村子中央的小河旁有一眼最大的泉,泉眼被凿成一个洗脸盆大的石钵,钵里的水永远是满满的、清清的,永远是新鲜的,多余的水溢出了石钵,流入了小河中。老乡们管这眼泉叫“井子”,全村吃水都靠它。这架山下去就是摩洼沟,那里的石崖缝缝上也有几眼泉,不知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泉眼边凿了一溜小槽儿,人站在那儿,嘴刚好能喝上泉水。就是这一溜溜儿泉眼,使我们干劲倍增。
到了山下,我撂下麦担,向着泉边奔去,一阵猛喝。一股股凉凉的、甜甜的甘露滋润了干裂的嘴唇和喉咙,直流进我的心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了。段队长赶了下来,大声喊着:“叶广荃,不敢把麦子撂下,那麦子干着哩,撂地下颗粒就全掉完哩!”有什么敢或不敢行或不行的,顾不上了!王蕴环、顾小容、董孟新、刘振农他们也全撂下麦子,飞也似的过来了,我们齐个展展地站成一溜溜儿在那水槽边喝水。男娃笑着喊:“看,饮驴哩。”一阵哄笑。
天刚刚亮,人们扛着麦担、拿着镰刀就上山了。那架山上是队里最好的麦地,人们都在低着头、双手不停地忙着,只听见一阵阵唰唰的割麦声,那声音里带着人们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老乡说是托了我们知青的福,今年的麦子大丰收。
一片片的麦子倒下了,随后被迅速捆成捆,齐个儿展展地摆在收割完的地里。太阳照到了坡上,到了回去吃早饭的时辰了,是不能空手回的,还得把捆好的麦子从山上担回场院里。麦担和普通担水的扁担不同,两头没有挂桶的铁钩子,而是削成尖尖的。要想把这尖尖的两头分别插进两捆麦子里,再把它们担在肩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技术,又要力气。先是把麦担的一头插进麦捆,高高地举起,再把另一头插进另一捆麦子,然后才担在肩上。两大捆麦子没有百十斤,也有七八十斤,往肩上一压,腿直打晃。就这样一天上山割麦、下山担麦要往返几次,反正割下的麦当天都要担回场里。没担几趟,肩膀就磨破了。最要命的是第二天,当那两大捆麦子再一次压在又红又肿又破了的肩上时,真是欲哭无泪。
但最难熬的还是干渴。随着太阳的升高,湿透了的汗衫又被火辣辣的太阳烤干,嘴里连唾沫都没有一滴,全身干枯得像是点火就着。越来越渴,脑子里只有一个字:“水!”抬头望去,晴空万里,那天真是蓝,蓝得深,蓝得透亮,蓝得就像是浩瀚的大海,让你恨不得一头扎进去……我们割麦的速度越来越快,因为麦捆太多了,段队长就会下令往回送,这样就能下山找点儿水喝。
没想到因为干渴,竟加快了割麦的速度、增加了送麦的次数,形成了作业的良性循环。“回喽……”随着段队长一声嘶哑的呐喊,我迅速地插起两捆麦子,担起来飞快地往山下跑。还在割麦时,我早就琢磨好目标了,在这架山的下面不远处,就有泉。是那清凉、甘甜的泉水在诱惑着我、驱使着我。
陕北的村庄分布在塬上和沟里,山上即为塬上,沟里即为山下。凡是在沟里的村子,大多都有一条小河,顺着山沟从村里流过。刚分到后段家河,就听外村人说这儿的水可好哩,有好多眼泉。后段家河村子中央的小河旁有一眼最大的泉,泉眼被凿成一个洗脸盆大的石钵,钵里的水永远是满满的、清清的,永远是新鲜的,多余的水溢出了石钵,流入了小河中。老乡们管这眼泉叫“井子”,全村吃水都靠它。这架山下去就是摩洼沟,那里的石崖缝缝上也有几眼泉,不知什么年代的人们在泉眼边凿了一溜小槽儿,人站在那儿,嘴刚好能喝上泉水。就是这一溜溜儿泉眼,使我们干劲倍增。
到了山下,我撂下麦担,向着泉边奔去,一阵猛喝。一股股凉凉的、甜甜的甘露滋润了干裂的嘴唇和喉咙,直流进我的心田。世上再没有比这更舒服的感觉了。段队长赶了下来,大声喊着:“叶广荃,不敢把麦子撂下,那麦子干着哩,撂地下颗粒就全掉完哩!”有什么敢或不敢行或不行的,顾不上了!王蕴环、顾小容、董孟新、刘振农他们也全撂下麦子,飞也似的过来了,我们齐个展展地站成一溜溜儿在那水槽边喝水。男娃笑着喊:“看,饮驴哩。”一阵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