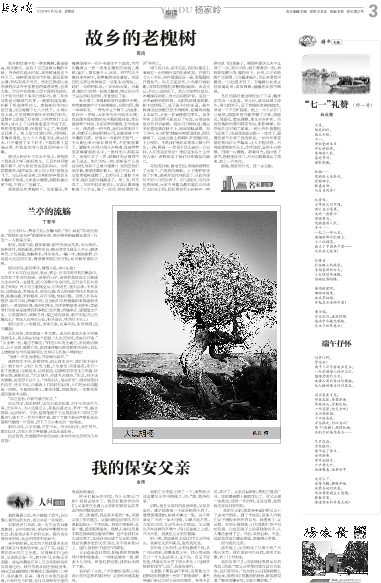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6月25日
故乡的老槐树
故乡的巷道中有一棵老槐树,极高极高,极老极老。没有人知道这棵古槐的年龄。爷爷说在他小时候,老槐树就是这个样子了。槐树据说是汉代所植,因没足够证据,显得有些不可信。然而它确实比黄帝陵的汉武帝手植柏显得要苍老些,也高大些。岁月在它的身上留下深深的刻痕,几个粗大的枝丫似乎已经枯死,第二年却又能冒出嫩绿的幼芽,一簇簇地摇曳着,和树干形成鲜明对比。老槐树的中间已经空透,里面能藏下七八个孩子。从树心往上看,可见茂密的树叶和刺眼的阳光。喜鹊在上面编了好多窝,引诱着我们上去掏蛋;成百上千只麻雀把这里当成了家,叽叽喳喳地叫着,呼啦啦飞走了,呼啦啦又回来了。树上是它们的世界,很热闹。老槐树很粗,七八个人合抱不住;树冠很大,几乎覆盖了半个村子,干枯的枝丫直插云霄,在我幼年的心里是那样高不可攀。
那时人民公社正在大干快上,老槐树下是社员们学习的好地方。几百名村民聚集在树下,听大队长传达最新指示。大家群情激昂,喊声震天,树上的小鸟扑棱棱全飞了。早晨天还没亮,洪亮的钟声便会从老槐树下传来,大家披衣戴帽,趿鞋执锄往树下跑,生怕上工迟到了。
我家就住在老槐树下。每年夏天,老槐树像撑开一把巨伞盖住半个庭院,弯弯的槐树虫一扭一扭地在细细的丝线上舞蹈,猛不丁落在脖子上,冰凉。邻里的几个媳妇坐在树下,围着槐荫说长道短。斑驳的阳光挤过叶隙落在一张张生动的脸上。她们一会窃窃私语,一会哈哈大笑。兴起时,媳妇们会唱一些陕北酸曲,路过的小伙子远远地驻足细听,不觉便红了脸。
秋天来了,老槐树伸展开无数只手臂,密密麻麻的叶片间挂满槐角,光滑圆润,像一串串翠玉。一帮伙伴立于树下,站成排,然后听一声喊,大家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我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爬到最高处,然后俯瞰整个村落,看家家炊烟缭绕,玉米金黄一片。槐角是一种中药,我们大把地折下来,待晾干后拿到药材公司,总能凑够下半学期的书费。记得有一次跟母亲怄气,一个人跑出来后躲在树洞里,不觉就睡着了。朦胧中,听见外面人声鼎沸,母亲带着哭音喊着我的名字,一条村的人都起来了。我匆忙应了一声,借着月光从树洞里走了出去。他们大吃一惊,说树里什么也没有呀,你在什么地方藏着?!我知道他们找不着,便谎说藏在树上。他们不信,说一定是老槐树成精了,上次你从上面掉下来不死,现在又把你藏起来了。第二天,母亲弄了二尺红布挂在树杈上,父亲对着老槐树磕了三个头,烧了一炷香,然后把我“系活”在树上。
树下有口井,深不见底,有时仅能在上面看见一小块镜片似的东西在晃。井索有七八十米长,盘在那里厚厚一圈,湿溜溜地冒着热气。每天天还没亮,小鸟便开始唱歌,闹哄哄的能把老槐树抬起来。天放亮后,井台上就热闹了。男人们排着队绞水,木桶撞在井壁上发出沉闷的声音。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树下凉快极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躲在树洞里捉迷藏已经不再稀奇,顺着树洞爬上去看书,才是一件最惬意的事儿。我常常在上面因看书而忘记了吃饭,从艳阳高照看到月明星稀。晚风习习地吹过,槐虫不经意地落在脖子上,凉凉地蠕动着。知了声声,小鸟悄悄地躲在树荫里休息,四周静极了。远处公路上的喇叭声时隐时现,十分悦耳。于是我们就趴在树杈上数小汽车,一辆,两辆……惊诧于那么高的一点空间,人在里面怎样坐?里面又坐些什么样的人呢?老槐树成了我们对外瞭望的窗口。
麦收的时候,雷电交加,老槐树被劈折了大枝丫,白晃晃的耀眼。上工的铁钟也掉了下来,滚到旁边的沟渠里了,从此再也听不到当当的钟声了。因为那时已实行承包责任制,大家不用集合都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间上地,因此再也看不到钟声一响群鸟乱飞的景象了。树洞在那次电火中又烧了一次,黑乎乎的,剩下薄薄的一层,却照样枝繁叶茂,槐花纷飞。后来,由于农药的广泛使用,小鸟越来越少,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一只也见不到了。老槐树从此真正地寂寞起来,孤孤恓恓,幽幽地在那里喘息。
冬日的斜阳透过树杈洒了下来,懒洋洋的没一点温度。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偌大的院子,没了老槐树浓浓的荫凉,显得一下子空旷起来。晚上一个人站在门口纳凉,隐隐听见有歌声飘了过来,很遥远,很遥远,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古老的槐树仿佛在眼前晃动,影影绰绰。钟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一树小鸟扑棱棱地飞起来了,顷刻便无影无踪……夜凉了,薄薄的雾气弄湿了我的脖颈,一如当年那葱绿的槐虫在心里蠕动,让人不能平静。月亮孤凄地挂在天上,冷冷清清,显得十分单薄。四周一片朦胧。踏着月光,我回到了家里,轻轻地推开门,月光也跟着我走了进来,地上一片灰白。
那晚,很好的月光。我一夜无眠。
那时人民公社正在大干快上,老槐树下是社员们学习的好地方。几百名村民聚集在树下,听大队长传达最新指示。大家群情激昂,喊声震天,树上的小鸟扑棱棱全飞了。早晨天还没亮,洪亮的钟声便会从老槐树下传来,大家披衣戴帽,趿鞋执锄往树下跑,生怕上工迟到了。
我家就住在老槐树下。每年夏天,老槐树像撑开一把巨伞盖住半个庭院,弯弯的槐树虫一扭一扭地在细细的丝线上舞蹈,猛不丁落在脖子上,冰凉。邻里的几个媳妇坐在树下,围着槐荫说长道短。斑驳的阳光挤过叶隙落在一张张生动的脸上。她们一会窃窃私语,一会哈哈大笑。兴起时,媳妇们会唱一些陕北酸曲,路过的小伙子远远地驻足细听,不觉便红了脸。
秋天来了,老槐树伸展开无数只手臂,密密麻麻的叶片间挂满槐角,光滑圆润,像一串串翠玉。一帮伙伴立于树下,站成排,然后听一声喊,大家争先恐后地往上爬。我总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爬到最高处,然后俯瞰整个村落,看家家炊烟缭绕,玉米金黄一片。槐角是一种中药,我们大把地折下来,待晾干后拿到药材公司,总能凑够下半学期的书费。记得有一次跟母亲怄气,一个人跑出来后躲在树洞里,不觉就睡着了。朦胧中,听见外面人声鼎沸,母亲带着哭音喊着我的名字,一条村的人都起来了。我匆忙应了一声,借着月光从树洞里走了出去。他们大吃一惊,说树里什么也没有呀,你在什么地方藏着?!我知道他们找不着,便谎说藏在树上。他们不信,说一定是老槐树成精了,上次你从上面掉下来不死,现在又把你藏起来了。第二天,母亲弄了二尺红布挂在树杈上,父亲对着老槐树磕了三个头,烧了一炷香,然后把我“系活”在树上。
树下有口井,深不见底,有时仅能在上面看见一小块镜片似的东西在晃。井索有七八十米长,盘在那里厚厚一圈,湿溜溜地冒着热气。每天天还没亮,小鸟便开始唱歌,闹哄哄的能把老槐树抬起来。天放亮后,井台上就热闹了。男人们排着队绞水,木桶撞在井壁上发出沉闷的声音。这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太阳热辣辣地照着,树下凉快极了,成了孩子们的乐园。躲在树洞里捉迷藏已经不再稀奇,顺着树洞爬上去看书,才是一件最惬意的事儿。我常常在上面因看书而忘记了吃饭,从艳阳高照看到月明星稀。晚风习习地吹过,槐虫不经意地落在脖子上,凉凉地蠕动着。知了声声,小鸟悄悄地躲在树荫里休息,四周静极了。远处公路上的喇叭声时隐时现,十分悦耳。于是我们就趴在树杈上数小汽车,一辆,两辆……惊诧于那么高的一点空间,人在里面怎样坐?里面又坐些什么样的人呢?老槐树成了我们对外瞭望的窗口。
麦收的时候,雷电交加,老槐树被劈折了大枝丫,白晃晃的耀眼。上工的铁钟也掉了下来,滚到旁边的沟渠里了,从此再也听不到当当的钟声了。因为那时已实行承包责任制,大家不用集合都知道自己应该什么时间上地,因此再也看不到钟声一响群鸟乱飞的景象了。树洞在那次电火中又烧了一次,黑乎乎的,剩下薄薄的一层,却照样枝繁叶茂,槐花纷飞。后来,由于农药的广泛使用,小鸟越来越少,再后来便销声匿迹,一只也见不到了。老槐树从此真正地寂寞起来,孤孤恓恓,幽幽地在那里喘息。
冬日的斜阳透过树杈洒了下来,懒洋洋的没一点温度。多年后,我又回到了故乡,偌大的院子,没了老槐树浓浓的荫凉,显得一下子空旷起来。晚上一个人站在门口纳凉,隐隐听见有歌声飘了过来,很遥远,很遥远,虚无缥缈,却又实实在在。古老的槐树仿佛在眼前晃动,影影绰绰。钟声就在这时响了起来,一树小鸟扑棱棱地飞起来了,顷刻便无影无踪……夜凉了,薄薄的雾气弄湿了我的脖颈,一如当年那葱绿的槐虫在心里蠕动,让人不能平静。月亮孤凄地挂在天上,冷冷清清,显得十分单薄。四周一片朦胧。踏着月光,我回到了家里,轻轻地推开门,月光也跟着我走了进来,地上一片灰白。
那晚,很好的月光。我一夜无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