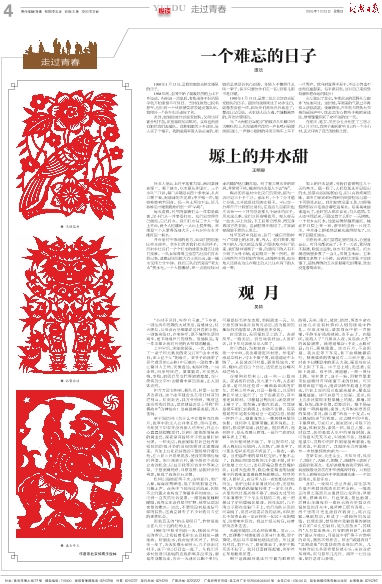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7月23日
塬上的井水甜
陕北人把山上的平地称为塬,南河寨就在塬上。塬上缺水,吃水要从井里打。三个小队三口井,每口井都足有四十多米深,从井口朝下看,黑漆漆的不见底;冲下喊一声,嗡嗡嗡地响着回音。扔一块土坷垃下去,好几秒钟后才能隐隐地听到一声“咕咚”。
每天清晨,村里的婆姨们头一件事是做饭,汉子们头一件事是打水。我们知青得自己做饭,自己打水。我们打水得三个人一起上井台,两个人摇辘轳,一人向上提井绳。常常是三个人累得浑身大汗,十五分钟左右才能打起一桶水。
井台是村中热闹的地方,知青们把那里比作王府井。老乡们笑话我们打水的样子,而村中壮汉们一个个打水的雄姿也确实让我们羡慕。一队女知青蒋玉莹曾为壮汉们打水掐过表,速度最快的数大力士刘长来,提一桶水仅用七分半钟。我们三队的男知青“老太太”贾永光,一个人摇辘轳,差一点被反转回来的辘轳把打翻在地。到了夏天用水多的时候,井常常干枯,解决的办法是人下去“掏”。
掏井的活是村中壮汉们的荣誉,因为一天可记三十个工分。那年月,十个工分才值七分钱,工分就是社员的命根子。平日每一分都斤斤计较的社员们,在这活儿面前谁也不去争——下井的总是那几个最壮的汉子。用水这么难,我们只好省喝俭用。每人每天一盆水,早上洗脸,下工后用它擦身,擦完身再用它洗衣服。直到脏得不能用了,才泼到窑洞前干燥的土地上。
村里的老乡说起水,总有一副自得的神气:“咱塬上的水好,甜,养人。你们看看,那沟下的人,吃水倒是方便,但那水吃不得!”后来,我们留神观察了一番,的确沟下的人有不少得了大骨节病,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所以虽然沟下的村里有沟水,还能种水稻,但当地人还是认为住在塬上的人比住在沟下的人高一等。
塬上的井水是甜,可我们也曾喝过几十天的臭水。那一阵子,人们发现从井里提出的水,经常有些短短的白毛,而且有股难闻的味。老乡们家家都用筛面的细箩把水过滤一下再倒进水缸。我们知青没那工具,只得慢慢捞那些白毛凑合着吃这臭水。后来臭味越来越大了,全村的人都在议论,有人瞎猜,有人还叫骂起来,可那又管什么用?一天傍晚,一个老乡去打水,他觉得辘轳越摇越沉。桶到井口提上来一看,原来桶里有一只死羊羔。羊羔身上的毛早就被水泡得脱光了,只剩下团团红线虫。
消息传来,我们望着缸里的臭水,心里直恶心。可月亮都老高了,干了一天活,累得直不起腰,晚饭还没做,这水不用也得用。把水倒进锅里多煮了一会儿,再倒玉米面。玉米糊糊又多熬了十分钟。出锅时大家肚子早就饿了,那热腾腾的玉米面糊糊吃到嘴里,谁也没觉着臭味来。
每天清晨,村里的婆姨们头一件事是做饭,汉子们头一件事是打水。我们知青得自己做饭,自己打水。我们打水得三个人一起上井台,两个人摇辘轳,一人向上提井绳。常常是三个人累得浑身大汗,十五分钟左右才能打起一桶水。
井台是村中热闹的地方,知青们把那里比作王府井。老乡们笑话我们打水的样子,而村中壮汉们一个个打水的雄姿也确实让我们羡慕。一队女知青蒋玉莹曾为壮汉们打水掐过表,速度最快的数大力士刘长来,提一桶水仅用七分半钟。我们三队的男知青“老太太”贾永光,一个人摇辘轳,差一点被反转回来的辘轳把打翻在地。到了夏天用水多的时候,井常常干枯,解决的办法是人下去“掏”。
掏井的活是村中壮汉们的荣誉,因为一天可记三十个工分。那年月,十个工分才值七分钱,工分就是社员的命根子。平日每一分都斤斤计较的社员们,在这活儿面前谁也不去争——下井的总是那几个最壮的汉子。用水这么难,我们只好省喝俭用。每人每天一盆水,早上洗脸,下工后用它擦身,擦完身再用它洗衣服。直到脏得不能用了,才泼到窑洞前干燥的土地上。
村里的老乡说起水,总有一副自得的神气:“咱塬上的水好,甜,养人。你们看看,那沟下的人,吃水倒是方便,但那水吃不得!”后来,我们留神观察了一番,的确沟下的人有不少得了大骨节病,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所以虽然沟下的村里有沟水,还能种水稻,但当地人还是认为住在塬上的人比住在沟下的人高一等。
塬上的井水是甜,可我们也曾喝过几十天的臭水。那一阵子,人们发现从井里提出的水,经常有些短短的白毛,而且有股难闻的味。老乡们家家都用筛面的细箩把水过滤一下再倒进水缸。我们知青没那工具,只得慢慢捞那些白毛凑合着吃这臭水。后来臭味越来越大了,全村的人都在议论,有人瞎猜,有人还叫骂起来,可那又管什么用?一天傍晚,一个老乡去打水,他觉得辘轳越摇越沉。桶到井口提上来一看,原来桶里有一只死羊羔。羊羔身上的毛早就被水泡得脱光了,只剩下团团红线虫。
消息传来,我们望着缸里的臭水,心里直恶心。可月亮都老高了,干了一天活,累得直不起腰,晚饭还没做,这水不用也得用。把水倒进锅里多煮了一会儿,再倒玉米面。玉米糊糊又多熬了十分钟。出锅时大家肚子早就饿了,那热腾腾的玉米面糊糊吃到嘴里,谁也没觉着臭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