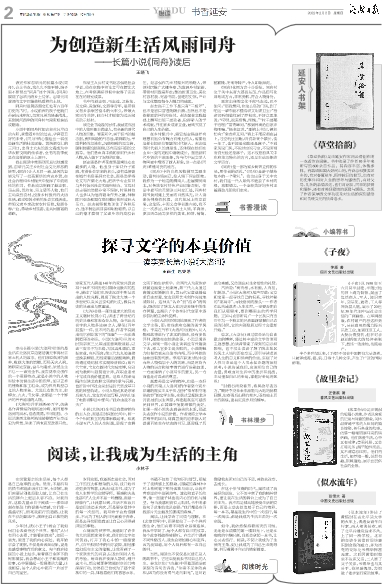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3月02日
探寻文学的本真价值
田雨生 赵秉勋
李亮长篇小说《大洛河》讲述的是生活在北洛河岸边婆娑镇无事湾村宗家五代人的故事。他们汲取洛河的滋养,收获大地的馈赠,历经天灾人祸,婚姻家庭变故,奋斗与追求,依然生生不息……读完全书,我发现李亮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仿佛生活中的原型,加以艺术的锤炼和加工组合,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尤其以女性为主,如蝉女、九丸、宝女等,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大洛河》洋洋洒洒60万字,仿佛是作者情绪的堤坝被冲垮,如同夏季洛河的洪水,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小说以陕西北洛河流域娑婆镇百年变迁史为背景,讲述了清末直至改革开放,宗家五代人跨越140年的家族兴衰史和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命运跌宕的故事,描述了他们在历史沉浮中所呈现出的人性光辉,展现了陕北大地一个多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极具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
《大洛河》是一部体量庞大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讲述了跨世纪的历史沧桑和家族众多人物。全书出现名字的人物多达60余人,酷似《百年孤独》一样,但不同的是,作者李亮跳出马尔克斯笔下的“怪圈”——无法逃脱循环的命运。小说《大洛河》从清末时期宗家三兄弟因匪患离散讲起,以老三安来子为主线,写其离乱漂泊,重振家业,由兴而衰;第三代九丸被迫接受换亲婚姻,历经家暴后觉醒离婚,最终通过缝纫技术实现经济独立;第五代宝童、宝女在新时代突破束缚,分别成为教师与服装设计师,在职业追求中完成自我价值重构。这些人物命运既体现陕北农耕文明的传承与瓦解,也折射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轨迹。小说人物尤其是宗家后辈九丸、宝女的命运写照,恰恰印证了电影《哪吒》中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小说《大洛河》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纵观小说五代人的人生际遇,展现了农耕文明下的生存哲学。前两代人为家族存续被迫接受土地束缚,第三代九丸通过离婚实现婚姻自主,第五代宝童退婚追求自由恋爱,宝女则用艺术创作突破地域限制。这种从“认命”到“改命”的转变,既体现了陕北人在历史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也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变革中逐步获得的主体性觉醒。
小说《大洛河》鲜明地展现了作者的文学主张,即:崇尚悲欢交融的美学风格。李亮在写作《大洛河》过程中,对人物和故事进行了忠实的叙述,没有多做评判,踏踏实实地讲故事。小说是通俗文学,如果一部小说让读者没有兴趣读下去,那么它多半是失败的。小说的魅力归根结底来自故事内部,而非外挂的抽象出来的判断。李亮在叙述过程中没有给人物强加个人的判断,而是用符合人物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进行准确叙述,一方面遵循了小说写作的要义,另一方面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真善美是文学的精神,也是一本好小说的灵魂。《大洛河》的作者坚守质朴深邃的现实主义手法,坚持“恪尽职守地讲故事”的文学主张,全景式呈现陕北洛河流域的民生图景,构建起真实可感的民间世界,在苦难中捕捉细微的美好。如果一部小说失去真善美的本质,那就失去创作小说的价值。作者秉持文学本质精神的回归,将真善美的追求融入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书写,既展现了历史沧桑感,又传递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古语说:“树有根,水有源,人有祖,知渊源。”小说《大洛河》尾声写道:宝女和宝童一起寻找自己的根系,寻找神秘的“琉璃寺”,寻找洛河的源头……作者在此告诫读者:人生在世,一定要弄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总之,《大洛河》通过宿命论与自由意志的博弈,通过其丰富的文学价值和主题思想,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它不仅让读者了解了陕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更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实现了对人性与命运这个人类永恒命题的深刻思考;小说告诫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掌舵好命运的风帆!
“时值谷雨染春芳,春风欲尽去远方。”期待李亮未来作品能与大地的脉搏同频,如春雨后山野的草木,既有破土而出的新绿,更有沉淀岁月的醇厚。
李亮长篇小说《大洛河》讲述的是生活在北洛河岸边婆娑镇无事湾村宗家五代人的故事。他们汲取洛河的滋养,收获大地的馈赠,历经天灾人祸,婚姻家庭变故,奋斗与追求,依然生生不息……读完全书,我发现李亮创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仿佛生活中的原型,加以艺术的锤炼和加工组合,成为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尤其以女性为主,如蝉女、九丸、宝女等,全都是一个个鲜活的普普通通的人物。
《大洛河》洋洋洒洒60万字,仿佛是作者情绪的堤坝被冲垮,如同夏季洛河的洪水,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小说以陕西北洛河流域娑婆镇百年变迁史为背景,讲述了清末直至改革开放,宗家五代人跨越140年的家族兴衰史和个体在不同历史时期命运跌宕的故事,描述了他们在历史沉浮中所呈现出的人性光辉,展现了陕北大地一个多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极具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
《大洛河》是一部体量庞大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讲述了跨世纪的历史沧桑和家族众多人物。全书出现名字的人物多达60余人,酷似《百年孤独》一样,但不同的是,作者李亮跳出马尔克斯笔下的“怪圈”——无法逃脱循环的命运。小说《大洛河》从清末时期宗家三兄弟因匪患离散讲起,以老三安来子为主线,写其离乱漂泊,重振家业,由兴而衰;第三代九丸被迫接受换亲婚姻,历经家暴后觉醒离婚,最终通过缝纫技术实现经济独立;第五代宝童、宝女在新时代突破束缚,分别成为教师与服装设计师,在职业追求中完成自我价值重构。这些人物命运既体现陕北农耕文明的传承与瓦解,也折射中国社会从封建时代到改革开放的转型轨迹。小说人物尤其是宗家后辈九丸、宝女的命运写照,恰恰印证了电影《哪吒》中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小说《大洛河》全书没有贯穿始终的主人公,而是在时间的长河中,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串联起来。纵观小说五代人的人生际遇,展现了农耕文明下的生存哲学。前两代人为家族存续被迫接受土地束缚,第三代九丸通过离婚实现婚姻自主,第五代宝童退婚追求自由恋爱,宝女则用艺术创作突破地域限制。这种从“认命”到“改命”的转变,既体现了陕北人在历史夹缝中的生存智慧,也揭示了个体在时代变革中逐步获得的主体性觉醒。
小说《大洛河》鲜明地展现了作者的文学主张,即:崇尚悲欢交融的美学风格。李亮在写作《大洛河》过程中,对人物和故事进行了忠实的叙述,没有多做评判,踏踏实实地讲故事。小说是通俗文学,如果一部小说让读者没有兴趣读下去,那么它多半是失败的。小说的魅力归根结底来自故事内部,而非外挂的抽象出来的判断。李亮在叙述过程中没有给人物强加个人的判断,而是用符合人物的语言和故事情节进行准确叙述,一方面遵循了小说写作的要义,另一方面也是对读者的尊重。
真善美是文学的精神,也是一本好小说的灵魂。《大洛河》的作者坚守质朴深邃的现实主义手法,坚持“恪尽职守地讲故事”的文学主张,全景式呈现陕北洛河流域的民生图景,构建起真实可感的民间世界,在苦难中捕捉细微的美好。如果一部小说失去真善美的本质,那就失去创作小说的价值。作者秉持文学本质精神的回归,将真善美的追求融入对普通百姓生存状态的书写,既展现了历史沧桑感,又传递出对生命韧性的礼赞。
古语说:“树有根,水有源,人有祖,知渊源。”小说《大洛河》尾声写道:宝女和宝童一起寻找自己的根系,寻找神秘的“琉璃寺”,寻找洛河的源头……作者在此告诫读者:人生在世,一定要弄明白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哲学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民族只有当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重新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它的内部发展过程才会重新开始。”
总之,《大洛河》通过宿命论与自由意志的博弈,通过其丰富的文学价值和主题思想,给读者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和影响。它不仅让读者了解了陕北地区的风土人情和历史变迁,更引导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和活着的价值,实现了对人性与命运这个人类永恒命题的深刻思考;小说告诫我们,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勇敢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挑战,主动把握自己的命运,掌舵好命运的风帆!
“时值谷雨染春芳,春风欲尽去远方。”期待李亮未来作品能与大地的脉搏同频,如春雨后山野的草木,既有破土而出的新绿,更有沉淀岁月的醇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