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5月05日
张超:在生活裂缝种字,生发抵抗平庸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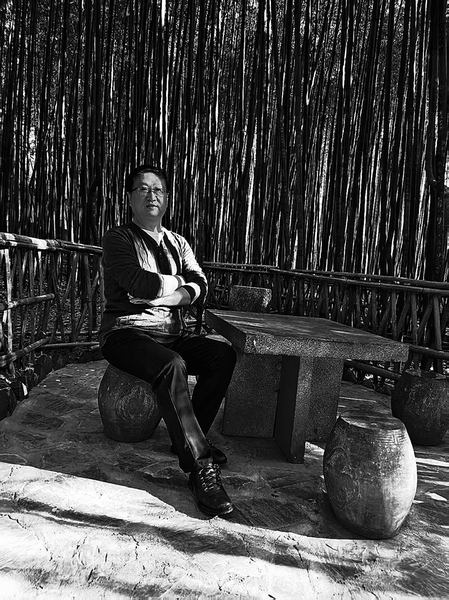 ● 嘉宾张超
● 嘉宾张超 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学力量。今天做客我们《作家说》栏目的作家,是宝塔区政协《见闻》刊物责任编辑、延安市作协会员、宝塔区作协副主席、延安市图书馆理事会常务理事张超。
张超,陕西佳县人,生于1967年4月,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现为延安市工程造价管理办公室负责人。获2012年延安市科学技术成果一等奖,陕西省科技成果奖;获2016年度科技创新人物。工作之余,酷爱文学,喜好书法和摄影。多年笔耕不辍,创作诗歌、散文千余篇(首),发表于《陕西日报》《廊坊日报》《中国审计》《延安文学》《延安日报》《见闻》等报刊。2018年创建微信公众号《朴学书屋》。胡琛:写作于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张超:写作于我而言,是一种灵魂的自由,是作为人的精神行为。选择写作,也就是选择了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表达。我不是专业作家,也不是一线作家,我经常讲离“家”还有一段距离。而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学艺术的热爱者、追寻者,甚至是一个勇敢的探索者,总爱把生活揉成散片来写,当然也与我的工作属性和时间有一定关系。我真正的专业是土木建筑工程,是一名高级工程师,可以说我是一名业余写作者,因为酷爱文学艺术,就像禾苗在田地里不可抑制地生长。就这样我开始写作,二十余年走过来了。
我写的题材主要有散文、诗歌及小小说。我对散文尤为钟情,以为散文是心灵的独语,无需迎合众意,不必拘于格套,随心随性,直抒胸臆,或喜或悲,或忧或怒,皆从心出,真诚无伪。它是心灵深处的声音,是灵魂的独白,是自我与本真的回归。谈起我的写作,可以分为过去、现在、将来三部分。
胡琛:请您先从过去开始聊起。
张超:好的,谈到写作,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著名作家路遥。对于六十年代出生的人而言,当指尖轻触稿纸,记忆的褶皱里总会浮现出那个戴着宽边眼镜、面容沧桑的身影——路遥。在改革开放初期的精神荒原上,路遥的文字如同黄土地上的信天游,以粗粝而滚烫的笔触,为一代人搭建起照进现实的理想主义灯塔。
读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那些浸透汗水与泪水的奋斗故事,恰与我们自身的成长轨迹形成共振,既背负着传统价值的厚重行囊,又怀揣着走向更广阔世界的热望。路遥笔下的人物从来不是完美的英雄,而是在苦难中挺直脊梁的“平凡者”,这种对普通人精神史诗的书写,让六十年代的写作者们第一次在文学中找到了自己的镜像:原来黄土地的沟壑里,藏着动人的生命诗篇。
更重要的是,路遥本人的创作生涯本身就是一部热血传奇。他像苦行僧般扎根陕北,用近乎自虐的方式搜集素材、打磨文字,甚至为写作《平凡的世界》查阅十年报纸,最终倒在文学的征途上。路遥的存在依然在提醒:真正的文学,永远与土地上的悲欢休戚与共。
工作之余,读书和写作始终是我的爱好和追求。幸运的是,我第一个工作岗位便是城乡规划管理,踏勘规划选址现场和测绘地形地貌是日常工作,恰恰给我提供了一路拍摄记录生活中的人文景观、自然景观的机会。实际上,引领我走上写作之路的第一位老师是高其国,现为《华圣文化》主编。很早之前,高其国在延安市文联工作,多次来规划局办事。一天,我怯怯地拿出偷着写下的若干篇散文和诗歌欲请高老师指导,他浏览后带走一首诗歌、一篇散文文稿,居然先后在《华圣文化》刊物发表,成了我写作的源动力。
胡琛:聊完了过去,聊一聊您的现在。
张超:8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延川县永坪镇段家圪塔村行门户,随后我把老村走了一遍,居然发现老村完整保留了原来的历史风貌,段思英将军就是从这里的窑洞走上革命道路的。40多个来自北京清华附中的知青曾在这里插队,陶海粟是北京知青的代表人物,为村里做了许多实事。于是,我萌发了保护和传承古村文化的想法。
一个粗糙的开始,往往是最好的开端。我与文友陈梦远、白舟波、景文瑞、周春等自己动手,清除院子蒿草,平整院落,用黏土砖铺地面,用石头胶粘接石板做展台,解决缺少柜子的问题。随后,更多的文友、书友、摄友等参与进来,发挥各自所长,帮畔、搭凉亭、砌艺术墙,继而植树种草。自诩名为“乡村文化驿站”。为了丰富文化驿站内容,我们创办了延安古村书画院,一孔窑洞用于书画陈列,一孔窑洞用于知青文化陈列,一孔窑洞作为民俗文化陈列。一些活动都依托院落和凉亭开展,虽然小,但让我有了更多的机会体验乡村。与四方朋友的交流,给我的写作注入了巨大的力量。
还记得初到这里时,已故岳父曾住过的院落,在岁月的侵蚀下破败不堪,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决心为它注入新的生命力,于是一场精心的修葺工程开启。我在这座古老的院落里融入传统历史文化元素,让它摇身一变,成为独具乡村特色的文化院落——采风文化驿站。我希望它能成为文化的汇聚地,吸引更多人探寻乡村的魅力。没想到,这座小小的院落,如同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泛起层层涟漪。它竖起了文化标杆,带动了村史馆的建设,唤醒了部分村民对老村老窑的保护意识。他们纷纷效仿,自觉保护与恢复自家院落,让古村的原生态风貌得以延续。
值得感谢的另一位老师是著名作家史小溪。他的散文在延安、西北乃至全国都颇有影响。我们既师亦友。受史小溪老师书籍作品的影响和茶饭交流中的潜移默化,我的散文确有进步。
事实上,有一大批作家,如刘成章、侯波、厚夫、张金平等等,俨然像高山、像森林、像江河,牵引着延安文学艺术向高地挺进……
我的作品以散文为主,诗歌次之。写作中坚持生活为底色,以乡村、人文为支撑,以研学旅行为路径。同时,积极开展文化寻访,虚心取经,努力提升文化素养。
近几年,颇喜欢读传记,尤其是文学作家的传记。从《柳青传》到《路遥传》《路遥别传》,又到《陈忠实传》,再到《贾平凹传》……震撼心灵,直击灵魂,似有凤凰涅槃、脱胎换骨之意,继而醒悟人生。
2018年,我创建“朴学书屋”公众号,在延安网信办备案。发表近20万字的诗歌散文,无打赏、无广告、无盈利。以接地气式的生活、研学、旅行和文化寻访开展以诗歌、散文为主要题材的创作。
我常常称“朴学书屋”公众号是我和文友及文学爱好者的文化驿站,而段家圪塔古村文化小院是我们的采风文化驿站。其中的乐趣和意义,唯有身临其境方可领略,不是所有人能理解和体验到的。筑梦的情怀,是在自己的世界里,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奇迹。
2025年元月8日,一则来自延安电视台记者的消息,如同一束强光,刹那间照亮了延川县段家圪塔古村的宁静角落。当我收到“游乡村,话年俗”的拍摄文案时,我就知道,古老的年俗即将在这片质朴的土地上,通过镜头的捕捉,向世人展现其独特魅力。
这4年多来,段家圪塔村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宾朋。有前来考察的学者,有乡村游的客人,有十里八乡的农邻,还有来自省内外的学者友人,粗略估算已有3000余人到此。他们的到来,为这座古老的村庄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新质生产力,亦带去了陕北古村的厚重魅力和包容好客。乙巳春节前,延安电视台和延安市政协原主席、文化学者樊高林共同选定在段家圪塔村拍摄《巳巳如意话年俗》专题片,无疑为古村搭建了一个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有机会认识它、了解它、走近它,关注段家圪塔村的过去,给力段家圪塔村的现在,携手共建段家圪塔村的未来,振兴乡村。
胡琛:接下来我们聊一聊您对未来的展望。
张超:有人说业余写作是场漫长的单恋,永远在等命运的回信。我只是觉得心里有团火,必须找个出口。出自己的专辑是我定下的三年目标: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一本摄影集。目前均在有序推进。
出专辑是专业出版社对作家作品的一种认同,当然这不是唯一,重要的是读者的认同。我以为真正的写作,是把平凡日子里的褶皱都轻轻抚平,让光漏进来。或许终其一生,我都会是个在现实与文字间游走的业余作者,但这又何妨?只要灵感的火星还在跳动,只要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仍在记忆里发光,就永远有写下一个句子的冲动。而这,已经是最美好的展望了。
那些被现实切割的碎片时间,恰是写作最真实的土壤——当我们不再等待“完整的时间”,而是学会在生活的裂缝里播种,文字便有了抵抗平庸的力量。
真正的写作训练,始于对“无用细节”的收集癖。业余写作者的优势正在于此:不必被专业写作的框架束缚,反而能以素人视角捕捉到职业作家熟视无睹的真实——那些藏在标准化生活背后的褶皱,正是人性最鲜活的肌理。跟着心跳的节奏走,而非跟着他人的脚印。
写作的意义,于我而言,是眼睛与心灵同频发现美(丑有时也是一种美)而通过文字密码记录下来,又是自我的诚实解剖。写作让我们在被压抑的小氛围跳出来,得以畅快呼吸、吐纳、愉悦。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建立跨越时空的隐秘连接。当某个读者说“你的文字让我想起了某个人”,那些曾被视为“无用”的细节突然有了重量。写作是一场静默的对话,作者与读者在文字的褶皱里交换体温。这种超越功利的共鸣,让孤独的写作变成了集体的心跳。
对抗遗忘,是写作最朴素的使命。我们写下的每个字,都是在为平凡日子钉上一枚记忆的钉子。站在现实与虚构的交界处,每个业余写作者都是举着微小火把的旅人。我们不奢求照亮整个世界,只愿让火把的光芒映亮眼前的方寸之地,让那些在生活中低头赶路的人,偶尔抬头能看见:在标准化的微笑与寒暄之下,还有无数值得被记录的、带着体温的细节,正在文字的土壤里悄悄生长。这或许就是写作最根本的意义:在坚硬的现实里凿出裂缝,让光与故事一起流淌,既温暖自己,也照亮某个未知的角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