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9月29日
鲁艺:将艺术转化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和思想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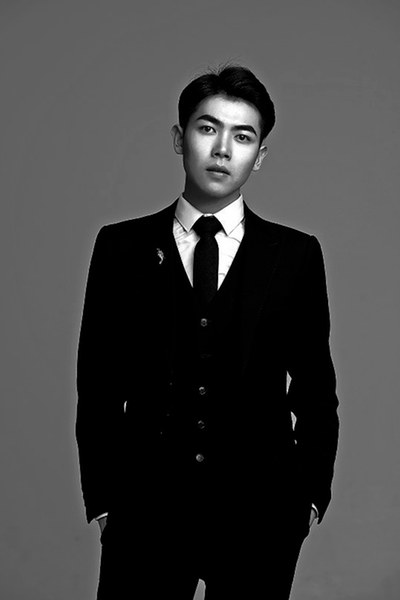 主持人陈晨:当年位于延安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为延安文艺战线的大后方,是抗日战争中一条不可或缺的“文化生命线”。它以文艺为媒介,不仅在战时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文艺的新纪元,确立了文艺与人民、与时代、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深刻启示我们,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源泉。
主持人陈晨:当年位于延安桥儿沟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作为延安文艺战线的大后方,是抗日战争中一条不可或缺的“文化生命线”。它以文艺为媒介,不仅在战时起到了“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打击敌人”的巨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文艺的新纪元,确立了文艺与人民、与时代、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优良传统。这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深刻启示我们,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实现伟大梦想的精神源泉。  主持人远播:本期的《文艺抗战——延河畔的救亡音符》鲁艺文化中心特辑我们邀请到了鲁艺文化中心宣教部的鲁慧,和我们一同追寻那段抗战文艺的烽火岁月。
主持人远播:本期的《文艺抗战——延河畔的救亡音符》鲁艺文化中心特辑我们邀请到了鲁艺文化中心宣教部的鲁慧,和我们一同追寻那段抗战文艺的烽火岁月。  ● 嘉宾鲁慧
● 嘉宾鲁慧 陈晨:作为抗战时期最重要的文艺阵地,鲁艺是如何响应“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号召的?
鲁慧:抗战时期,鲁艺作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实施统一战线下的抗战文艺教育。1938年4月10日,鲁艺宣告成立,《成立宣言》进一步指出:越当敌人加紧进攻的时候,我们越感觉到成立这个学院的迫切需要。它从成立之初就坚决贯彻“文艺为抗战服务”的宗旨,将艺术创作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它不是一座象牙塔,而是一座直接面向战场、面向群众的文艺堡垒。具体来说,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方向指引,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鲁艺乃至全国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根本方向;二是组织保障,鲁艺师生组成了众多文艺工作团、宣传队,直接开赴前线、深入乡村,进行战地演出和宣传动员;三是在创作实践中,鲁艺诞生了《黄河大合唱》《白毛女》《兄妹开荒》等大量融合民族形式与抗战主题的文艺作品,涵盖音乐、戏剧、美术、文学等领域,以大众化、战斗化的艺术形式激发群众抗战热情,真正让文艺成为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远播:冼星海等艺术家是如何将民族危亡转化为艺术语言的呢?
鲁慧:抗日战争14年,是一个血与火的年代,也是歌咏全民族抗战的年代。在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危难关头,需要用歌声唤起民众、凝聚人心。
《黄河大合唱》诞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是由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和诗人光未然联袂谱写的。1939年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三队队长光未然因在前线坠马受伤,左臂骨折,来到延安疗伤。好友冼星海得知消息后前去医院探望,两人在病榻上达成了再合作一次的意向。
之后,光未然按捺不住创作的冲动,在病床上用5天的时间,将自己两次渡过黄河,目睹船夫们与狂风恶浪搏斗的情景与在吕梁山两个多月的战斗经历,一气呵成,浓缩成了400行的长诗,作为《黄河大合唱》的歌词。
3月11日,演剧三队在延安西北旅社驻地窑洞里举行了朗诵晚会,在一盏极其昏暗的油灯旁,诗人光未然用低沉的声音朗诵了《黄河船夫曲》《黄河颂》《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水谣》《黄河怨》《保卫黄河》《怒吼吧,黄河!》八个部分的《黄河大合唱》的歌词。诗人的激情感染着窑洞里的每一个人,当诵咏声戛然而止的瞬间,冼星海上前一把抓住歌词,激动地大声喊道:“我有把握把它谱好!”
冼星海在拿到歌词的几日里,夜以继日地谱曲,经过六天六夜的时间,冼星海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八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黄河大合唱》的诞生,歌颂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光荣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痛诉日本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灾难,展现了抗日战争广阔的壮丽图景,并向全中国全世界发出民族解放的战斗警号,从而塑造起中华民族巨人般的音乐艺术形象,唱出了一个时代的最强音。
以冼星海同志为代表的鲁艺艺术家,他们的伟大之处在于将个人卓越的艺术才华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沉关切完美结合。他们深入生活、从民间音乐和现实苦难中汲取创作养分,用民族的苦难、悲愤的情绪为《黄河大合唱》谱曲。这部作品自问世以来,从延安传遍全中国,传向世界,它不仅塑造了黄河作为民族精神的象征意象,更将悲愤的情绪转化为战斗的力量,以音乐凝聚民心、鼓舞士气,成为振奋全天下中华儿女夺取民族解放战争不朽的精神力作。
陈晨:2025年,不仅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民族歌剧《白毛女》首演80周年。80年前,这部诞生于延安鲁艺的民族歌剧,不仅是中国革命文艺的里程碑,更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它如同一颗火种,照亮了无数人的心灵,那这部民族歌剧在抗战时期又发挥了怎样的时代价值?
鲁慧:《白毛女》的时代价值是超越其艺术价值的。1944年,西战团从晋察冀回到延安,全团并入了鲁艺。他们带回了晋察冀流传的“白毛仙姑”传说,于是鲁艺组织全院精英创作编排了大型歌剧《白毛女》,成为新中国民族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1945年,鲁艺为七大献演歌剧《白毛女》。当剧演到高潮,喜儿被救出山洞,背景音乐响起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歌声时,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以及观众们全体起立,长时间鼓掌。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传达中央书记处三点意见: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该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
歌剧《白毛女》在抗战即将胜利、国内矛盾亟待厘清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巨大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启蒙作用。它深刻揭示了旧社会的罪恶,通过喜儿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封建压迫的残酷,明确了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它歌颂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权带来的光明,极大地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同和对新社会的向往,激励了广大军民为“推翻旧世界、创造新社会”而继续奋斗,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奠定了深厚的群众思想基础。
远播:当年鲁艺的实验剧团和学员们创作、排演了大量反映抗战生活、歌颂英雄、揭露敌人的话剧和新秧歌剧。比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秧歌剧,这些新秧歌剧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宣传了生产自救、抗日救国的道理,这些新的形式的剧种在当时起到了哪些积极作用?
鲁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鲁艺师生积极响应“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创作排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新秧歌剧,成为了革命文艺大众化的典范,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作用。第一,普及了抗战和生产知识。它们用最通俗易懂的陕北方言、活泼生动的秧歌形式,将“识字学习”“开荒生产”这些支持抗战的具体行动演绎出来,让不识字的农民也能看得懂、记得住、学得会。第二,鼓舞了军民士气。《兄妹开荒》等节目歌颂劳动英雄,展现了延安军民乐观向上、自力更生的精神风貌,极大地激励了边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的生产热情。第三,创新了文艺形式。它们是对民族民间艺术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文艺真正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成为了当时最有效、最受欢迎的宣传和教育工具,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陈晨:鲁艺在精神和意识形态层面对我们有哪些更深层的影响呢?
鲁慧:鲁艺最深层的影响,在于它塑造了一代文艺工作者的灵魂,奠定了中国新文艺的基石。它确立并践行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则,这成为了中国文艺发展始终不变的旗帜。它锻造了“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创作方法,至今仍是艺术创作的生命源泉。它培育了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师生们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创造了辉煌的文艺成果,这种精神财富无比珍贵。更重要的是,鲁艺通过文艺作品,成功构建了一种集体的文化认同和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它将共产主义理想、爱国主义情怀、民族解放使命,通过艺术的方式注入到千百万人的心中,凝聚了人心,形成了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合力。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塑造和引领,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建设和发展。
远播: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的影响绝非仅限于艺术领域。它成功地将艺术转化为强大的组织动员力量和思想武器,为抗日战争锻造了一支不可或缺的“文化铁军”。这支军队用歌声、画笔、戏剧和文字,有力地配合了军事和政治斗争,为唤醒民众、鼓舞士气、凝聚人心、最终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替代的历史性贡献。其“深入生活、服务人民”的文艺传统,至今仍是中国文艺创作的宝贵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