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0月20日
“泪蛋蛋”何以掉进全国人民的“酒杯杯”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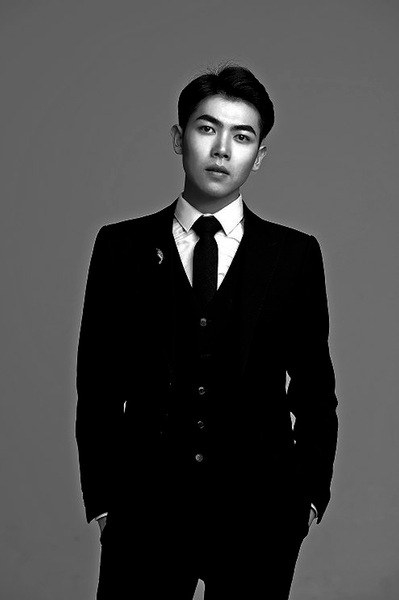

 ● 嘉宾李先锋
● 嘉宾李先锋 主持人陈晨: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本期《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我们邀请到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陕北民歌市级传承人李先锋,来分享他的音乐创作心得。
主持人远播:李先锋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尤其是他的《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一搭搭里》《我在延安等你》等歌曲被广为传唱,颇有影响。
陈晨:生活在延安这座城市,您有什么特别的感受?
李先锋:首先,延安这座城市到处都存在着历史的“节奏”。这从一系列的信天游歌曲到《黄河大合唱》等恢弘的大作中都可以体现。延安的底色是黄土地的浑厚,而它的声音,是信天游的高亢与抗战歌曲的激昂。冼星海在这里谱写出《黄河大合唱》,鲁艺的师生用音乐点燃民族的斗志。这些旋律不仅是战火中的号角,更是一种“音乐革命”,即用最朴素的民间音调,凝聚最磅礴的力量。对我而言,延安的音乐遗产启示深远,真正的艺术从不是孤芳自赏,而是与土地、人民同频共振。
其次,延安这座城无时无刻不充斥着精神的“和声”,它是一种苦难与信仰的交织。我曾站在这些窑洞旧址前,试图想象当年艺术家们如何在油灯下创作,如何用有限的乐器奏出无限的希望。延安精神中的“自力更生”,在音乐中体现为一种质朴的创造力。那就是没有钢琴,就用唢呐、腰鼓;没有乐谱,就向老乡学民歌。这种在限制中迸发出来的生命力,恰是我们当代音乐人需要的态度:回归本质,用真诚表达,用心去创作。
最后,延安这座城市是对当下生活的“变奏”,是历史文化古城与新时代节奏的对话。今天的延安,在宝塔山下的广场上、新城的大剧院里,仍有不少人唱着《山丹丹开花红艳艳》,还有好大一部分人都哼唱着现代的新陕北民歌。比如我的作品《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在延安传遍大街小巷,甚至传唱到全国。这座城市的魅力,正在于它从未被历史所固化,它允许信天游与新时代元素共同存在,让红色记忆与当代艺术碰撞。
远播:可以请您说说您在延安发展过程中的一些感受吗?
李先锋:延安的发展我们都有目共睹,它呈现出突飞猛进的态势。我作为一个音乐人,能工作生活在延安这片沃土上,并借着这片沃土独有的元素去创作,这可以说是生命对我的眷顾吧。
我是延长县人,之前一直在县剧团上班,刚调到延安工作时,我带着一种近乎朝圣的心情。我觉得延安这块革命圣地,应该是肃穆而厚重的,像一本泛黄的党史教材,记载着峥嵘岁月的每一道刻痕。但当我真正臣服于这片土地的时候,听见信天游在沟壑间回荡,看见街头老人用三弦弹唱着《东方红》时,我顿时就感受到,其实延安从未停留在历史里,它始终在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我觉得延安在“声音”里,从陕北民歌、信天游到现代乐器的完美融合就可体现。
记得有次在枣园旧址演出时,我录下了一位老农即兴演唱的信天游。他的嗓音沙哑却透亮,像黄土高原上刮过的风,带着颗粒感的真实。回到工作室,我将这段人声采样,混入电子鼓点与合成器音色,朋友听后惊讶:“这居然不违和!”我想,或许因为延安的精神本就是鲜活的,它从不怕被重新诠释。所以,我常常在创作遇到瓶颈的时候就去鲁艺旧址走走,那里让我沉思:当年冼星海用有限的资源创作出《黄河大合唱》,今天的我们拥有无数乐器和新时代技术手段,是否反而被工具束缚了表达的纯粹?或者又被时代提炼了精神实质的表达?但不管是什么情况,延安放在声音里去表达,也算是一种淋漓吧。
其次,我觉得创作时所用的“红色标签”,是地域赐予我的独特灵感。曾有人建议我写一首“标准的延安颂歌”,但当我试图套用宏大叙事时,旋律却变得僵硬。直到某天在延河边,看见几个孩子用石子打水漂,嬉笑着模仿广播里的红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延安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符号,而是具体的人如何在历史中生活。后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时,我完成的曲子《百年畅想 中华中华》,就是用小号作为前奏进入,体现了恢弘的气势,其中的低音部表现黄土的沉淀,副歌也激昂向上,我对这首歌的创作很是满意。所以,就单从音乐的角度,就能感受到延安的发展,更不要说经济文化等方面了。延安这座城市的魅力,就在于它永远允许你以最新颖的方式,成为它旋律的一部分。
在延安,历史不是压在肩上的重担,而是托起未来的手掌。作为音乐人,我们不必做小心翼翼的传承者,而可以成为大胆的“翻译官”——把黄土地的呼吸,变成能让世界听懂的音符。
远播:延安的生活经历,或者说延安的文化符号对您的工作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先锋:我是延长县人,12岁就进入延长戏剧学校学习二胡、板胡,后来在沈阳军区服役时,又学习了打击乐,2007年,我有幸通过考试进入志丹县歌舞团,因为不断努力学习音乐创作,又得以调到延安市曲艺馆工作。我感恩音乐,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音乐都是我的全部。在此期间,我创作了很多的音乐作品,深受延安人民的喜爱,比如《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一搭搭里》《我在延安等你》等歌曲广为传唱。要说延安的文化符号对我产生的影响,我想就是这种文化符号重塑了我的音乐灵魂吧。
作为一个音乐人,延安对我的影响不是一场简单的文化采风,而是一次彻底的声音启蒙。在这里,我感觉到了音乐心跳,也重新理解了创作与土地、人民、历史的关系。延安的生活经历和文化符号,像一组不断变奏的动机,持续影响着我的创作方式和音乐理念。完美的声音是放在特定环境去欣赏的,延安的民歌真正的感染力往往来自“不完美”,那些未经修饰的嗓音的粗粝感,反而让音乐更精致,有了生命感。这种“粗粝美学”让音乐不再只是听觉产品,而成了有温度的声音档案。
我认为延安的民歌、红歌、说书等文化符号一直是“历史遗产”。如今,当我闭眼去沉思延安时,浮现的不是静态的历史画面,而是一种动态的声音形成,这种主观意识形态的存在告诉我,伟大的音乐从来不是从真空里诞生的,它需要深扎在土地的裂缝中,倾听那些被忽略的杂音,最终长出自己的声音形状。而这,或许是延安给每一个音乐人最珍贵的礼物。所以每当我信心满满地搞创作时,我就会想起一句话——只有把麦克风对准大地,才能录到天空的回声。
陈晨:您在过往的生活和音乐创作经历中,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与我们分享?
李先锋:要说难忘的事儿,那可太多了。我父亲是陕北说书的艺人,打小就教我摆弄各种乐器,给我讲简单的乐理。那时候,我常跟着他去村里说书,听着弦子声和三弦响,慢慢爱上了音乐。
后来我开始自己写歌。在志丹县工作时,领导让我写首《这就是志丹》,专门唱志丹的。那天我熬到凌晨两点多,歌词和曲子怎么都不顺,实在写不下去,都打算跟领导说放弃了。然而第二天醒来,我想着再咬牙试试,结果真就把这首歌写完了。交上去后,领导还挺满意。从那以后,我写歌就越来越顺,像后来的新陕北民歌《一搭搭里》,好多人都爱听,周边省份唱陕北民歌的朋友,基本都能跟着哼两句。
要说最让我感动的,还是带着《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回延安演出那次。演完后,有位头发花白的大娘拉着我手说:“娃啊,原来你就是写这歌的,我太喜欢这首歌了,一听就想起年轻时等我老伴回家的日子。”听到这话,我心里特别暖。音乐能把不同年代人的故事串起来,让大家感同身受,这不就是我一直坚持创作的意义吗?
不管走到哪儿,延安的黄土地、窑洞前的烟火气,永远都是我写歌的灵感来源。
远播:未来,您的音乐创作有哪些规划和期待?
李先锋:我打算重点做新陕北民歌,既要守住传统文化的根,又得跟上时代的脚步。首先是保住陕北民歌的“魂”,像歌词里会保留“圪梁梁”“窑洞”这些当地话,旋律也延续信天游那种悠长的调子,让听的人一下子就觉得有陕北那味儿。同时,我想把现在的新故事唱进歌里,比如乡村振兴后窑洞改成民宿的变化,还有黄河边生态变好的景象,把这些写成“山丹丹花开在新窑洞前”“黄河湾里传来新渔歌”这样的歌词,让民歌既能讲好中国故事,又能让人听得懂、有画面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