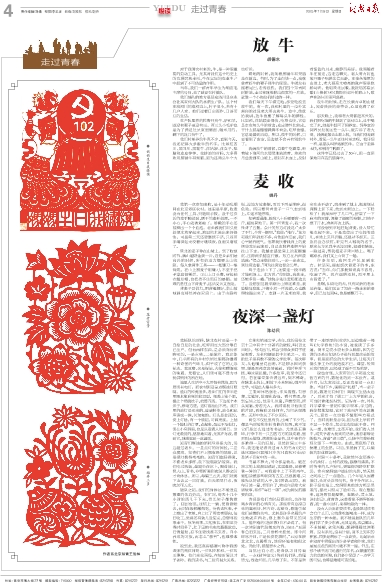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3年07月09日
放 牛
对于我国农村来说,牛,是一种很重要的劳动工具。尤其对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农耕民族来说,牛在实际的农业生产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当年,我们一群青年学生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了延安农村插队。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延安洛川县京兆公社高家河大队的水渭生产队。这个村在洛河川的洛河边上,村子很小,共有十几户人家。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生产队里养的牲畜只有牛、驴和羊,既没有骡子更没有马。两三头小毛驴也是为了满足社员家里磨面、碾米用的。剩下的就只有牛了。
我们村里养的牛真不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大多数牛的名字。比如红四川、黑四川、黑犍牛、洋姑娘、洋女子、梨脑和皮皮等等。我耕地的时候,大多喜欢用黑键牛和梨脑,因为这两头牛个大也听话。
耕地的时候,我架着黑键牛和梨脑走在前边。有时,为了走得快一点,我就拿着赶牛的鞭子捅牛的屁股。牛就左右摇着尾巴,走得很快。我们四个知青同时耕地,走过来就能耕出很宽的一片地,就像一个小拖拉机耕过的一样。
我们每天下午耕完地,都要轮流去放牛的。有一次,我和村里的一位朴实善良的社员老大哥去放牛。途中,他就给我讲,放牛也要了解每头牛的脾性。比如说,洋姑娘走得快,吃草也快,它总是走在每头牛的前边;皮皮脾性比较皮,干什么都是慢慢腾腾不着急,吃草也慢,它总是落到后边。所以,放牛的时候,只要看到了皮皮,后边就不会再有别的牛了。
我俩放牛的时候,看着牛吃着草,听着坡下洛河的水缓缓地流淌着。浓浓的月色泼洒在山坡上,照射在水面上,反射着银色的月光,幽静而美好。我俩随着牛往前走,边走边聊天。老大哥有时也放开嗓子唱陕北信天游。在夜色笼罩的山坡上,老大哥高亢嘹亮的歌声很是悠扬动听。他唱陕北民歌,我就唱苏联民歌《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声在洛河川里回荡着。
放牛的时候,走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闻着淡淡的青草香,心里充满了欢乐。
那天晚上,我和老大哥都挺高兴的。我们把吃饱的牛赶到了洛河边上,让牛喝完了水,就把牛赶回了饲养室。饲养室的饲养员发现还差一头牛,就告诉了老大哥。我俩赶紧去山坡上找。当我们刚走到村外,看见一头牛正往村里走呢。我仔细一看,是那头叫洋姑娘的牛。它由于走得太快,和别的牛脱群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50年,但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当年,我们一群青年学生为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了延安农村插队。
我们插队的地方是延安洛川县京兆公社高家河大队的水渭生产队。这个村在洛河川的洛河边上,村子很小,共有十几户人家。他们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生产队里养的牲畜只有牛、驴和羊,既没有骡子更没有马。两三头小毛驴也是为了满足社员家里磨面、碾米用的。剩下的就只有牛了。
我们村里养的牛真不少,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大多数牛的名字。比如红四川、黑四川、黑犍牛、洋姑娘、洋女子、梨脑和皮皮等等。我耕地的时候,大多喜欢用黑键牛和梨脑,因为这两头牛个大也听话。
耕地的时候,我架着黑键牛和梨脑走在前边。有时,为了走得快一点,我就拿着赶牛的鞭子捅牛的屁股。牛就左右摇着尾巴,走得很快。我们四个知青同时耕地,走过来就能耕出很宽的一片地,就像一个小拖拉机耕过的一样。
我们每天下午耕完地,都要轮流去放牛的。有一次,我和村里的一位朴实善良的社员老大哥去放牛。途中,他就给我讲,放牛也要了解每头牛的脾性。比如说,洋姑娘走得快,吃草也快,它总是走在每头牛的前边;皮皮脾性比较皮,干什么都是慢慢腾腾不着急,吃草也慢,它总是落到后边。所以,放牛的时候,只要看到了皮皮,后边就不会再有别的牛了。
我俩放牛的时候,看着牛吃着草,听着坡下洛河的水缓缓地流淌着。浓浓的月色泼洒在山坡上,照射在水面上,反射着银色的月光,幽静而美好。我俩随着牛往前走,边走边聊天。老大哥有时也放开嗓子唱陕北信天游。在夜色笼罩的山坡上,老大哥高亢嘹亮的歌声很是悠扬动听。他唱陕北民歌,我就唱苏联民歌《山楂树》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歌声在洛河川里回荡着。
放牛的时候,走在长满青草的山坡上,闻着淡淡的青草香,心里充满了欢乐。
那天晚上,我和老大哥都挺高兴的。我们把吃饱的牛赶到了洛河边上,让牛喝完了水,就把牛赶回了饲养室。饲养室的饲养员发现还差一头牛,就告诉了老大哥。我俩赶紧去山坡上找。当我们刚走到村外,看见一头牛正往村里走呢。我仔细一看,是那头叫洋姑娘的牛。它由于走得太快,和别的牛脱群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了50年,但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