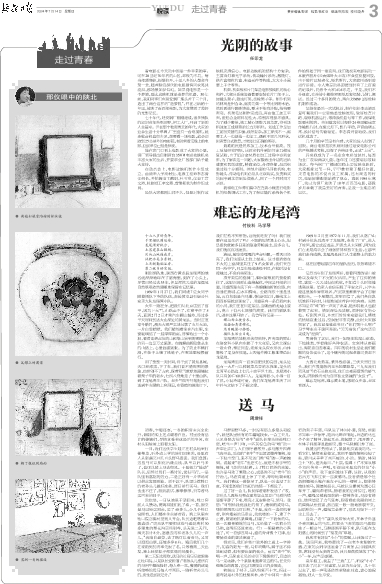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4年07月14日
光阴的故事
看电影在今天的中国是一件平常的事。可在20世纪70年代的山区,却极为不易。每当夜幕降临,银幕拉开,十里八乡的人都会齐聚一堂,随着跌宕起伏的电影剧情同欢笑共流泪,那场景如梦似幻。如果说电影是一个个梦境,那么放映机就是造梦的机器。50年前,我和同事们在延安钢厂埋头苦干三个月,造出了两台这样的“造梦机”,并在之后的十年里,放映了近百部电影,为大家增添了美好的光影记忆。
七十年代,延安钢厂刚刚建成,很多插队的知识青年告别田野,招工入厂,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厂里没有一台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很少见,想要看一场电影,就必须跑到25公里外的电影院,有时候看完晚上的电影,回到单位已经是深夜。
能在家门口看上电影成了大家的心愿,钢厂领导提出自制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来丰富大家的生活,并要求全厂各部门给予最大支持。
在动员会上,电影放映机制作小组成立。由清华大学高材生、电器工程师李志清任组长,并抽调电工魏明、杜玉堂,仪表工常文涛,机修钳工李文章、曾豫和我为制作组成员。
虽然大家都刚出师不久,但是对制作放映机充满信心。电影放映机的结构十分复杂,主要由灯箱光学系统、传动输片系统、激励灯、供片盒和收片盒、电器元件等构成,大大小小需要上千个零件。
机架、机架板和片门架是电影放映机的核心部件,大部分系统设备都要安装在片门架子上,如镜头架子、激励灯架、齿轮架子等。制作机架的材质是铝合金,需要先做一个等比例的木胎,然后再进行翻砂铸造,要求不能有沙眼,结构要密实。机架毛坯制作完成后,再由铇工加工平面,但铝合金材料韧性大,特别容易损坏道具。为了减少磨损,铇工精心调整刀具角度,将毛坯铝锭加工成规整的长方形铝块。划线工作是加工前很关键的步骤,线条复杂,加工深浅不一,需要工人一边划线一边加工,遇到不同几何形状,则需要公式推算,才能划出正确的图形。
最难的就是铣床加工,技术含量很高。铣工反复研究图纸,从固定机件到如何走刀都反复试验,由于铝合金材质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变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摸索出合适的进给速度和切削速度,精确定位,合理冷却,最后组装过程十分顺利。控制片速的马耳他机构、电影镜头、传动电机则必须从北京购买,负责购买的同事到北京到处找熟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买到。
我和电工师傅们集中在连铸小楼进行电影机的组装调试工作,为了保证输片系统各个机件始终处于同一垂直面,我们就找来电影院的一本废弃胶片《云南烟叶大丰收》在食堂反复回放,由于胶片已经老化,经常断片,大家就用透明胶进行拼接。令人难忘的是即便当时看了上百遍的纪录片,仍然令大家津津乐道。于是,我们不分昼夜,在连铸小楼按照图纸反复组装、试机、调试。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制作成功。
记得在最后一次试机前,制作组长李志清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熟悉放映流程,做好检查片路、观察机器运行、等待换机信号等工作,确保电影顺利放映。当间歇齿轮以每秒24格画幅速度传输影片时,在聚光灯下,影片平稳,声音曲调正常,换片信号传输稳定。李志清兴奋地说,我们试机成功了。
几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大家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两台电影放映机顺利通过延安电影公司的严格测试考核,取得了合格证书,正式“上岗”。
后来我成为了一名业余电影放映员,每周为全厂放映两次电影,逢年过节还要增加放映场次。每当钢厂广播通知晚上要放映电影时,大家都像过节一样,早早拿着凳子摆好位置,来看电影的不仅有员工家属,还有周边的村民,电影屏幕跟前站满了观众。直到1984年离厂,我已为钢厂放映了10年近百部电影,那段岁月承载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
七十年代,延安钢厂刚刚建成,很多插队的知识青年告别田野,招工入厂,开启了新的人生篇章。但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大家的业余生活十分单调,厂里没有一台电视机,就连收音机也很少见,想要看一场电影,就必须跑到25公里外的电影院,有时候看完晚上的电影,回到单位已经是深夜。
能在家门口看上电影成了大家的心愿,钢厂领导提出自制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来丰富大家的生活,并要求全厂各部门给予最大支持。
在动员会上,电影放映机制作小组成立。由清华大学高材生、电器工程师李志清任组长,并抽调电工魏明、杜玉堂,仪表工常文涛,机修钳工李文章、曾豫和我为制作组成员。
虽然大家都刚出师不久,但是对制作放映机充满信心。电影放映机的结构十分复杂,主要由灯箱光学系统、传动输片系统、激励灯、供片盒和收片盒、电器元件等构成,大大小小需要上千个零件。
机架、机架板和片门架是电影放映机的核心部件,大部分系统设备都要安装在片门架子上,如镜头架子、激励灯架、齿轮架子等。制作机架的材质是铝合金,需要先做一个等比例的木胎,然后再进行翻砂铸造,要求不能有沙眼,结构要密实。机架毛坯制作完成后,再由铇工加工平面,但铝合金材料韧性大,特别容易损坏道具。为了减少磨损,铇工精心调整刀具角度,将毛坯铝锭加工成规整的长方形铝块。划线工作是加工前很关键的步骤,线条复杂,加工深浅不一,需要工人一边划线一边加工,遇到不同几何形状,则需要公式推算,才能划出正确的图形。
最难的就是铣床加工,技术含量很高。铣工反复研究图纸,从固定机件到如何走刀都反复试验,由于铝合金材质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变形,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家摸索出合适的进给速度和切削速度,精确定位,合理冷却,最后组装过程十分顺利。控制片速的马耳他机构、电影镜头、传动电机则必须从北京购买,负责购买的同事到北京到处找熟人,用了一个月时间才买到。
我和电工师傅们集中在连铸小楼进行电影机的组装调试工作,为了保证输片系统各个机件始终处于同一垂直面,我们就找来电影院的一本废弃胶片《云南烟叶大丰收》在食堂反复回放,由于胶片已经老化,经常断片,大家就用透明胶进行拼接。令人难忘的是即便当时看了上百遍的纪录片,仍然令大家津津乐道。于是,我们不分昼夜,在连铸小楼按照图纸反复组装、试机、调试。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两台35MM电影放映机制作成功。
记得在最后一次试机前,制作组长李志清反复叮嘱我们一定要熟悉放映流程,做好检查片路、观察机器运行、等待换机信号等工作,确保电影顺利放映。当间歇齿轮以每秒24格画幅速度传输影片时,在聚光灯下,影片平稳,声音曲调正常,换片信号传输稳定。李志清兴奋地说,我们试机成功了。
几个月的辛苦没有白费,大家的投入得到了回报。两台电影放映机顺利通过延安电影公司的严格测试考核,取得了合格证书,正式“上岗”。
后来我成为了一名业余电影放映员,每周为全厂放映两次电影,逢年过节还要增加放映场次。每当钢厂广播通知晚上要放映电影时,大家都像过节一样,早早拿着凳子摆好位置,来看电影的不仅有员工家属,还有周边的村民,电影屏幕跟前站满了观众。直到1984年离厂,我已为钢厂放映了10年近百部电影,那段岁月承载了我最美好的青春,是我一生难忘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