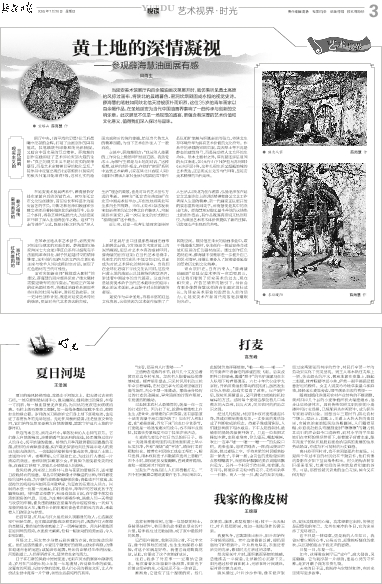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7月20日
打麦
“快看,那里有人打麦喽——”
正值梅杏成熟的季节,我与几个文友沿着黄河岸边乡村采风。忽然有人指着远处惊喜地喊道。顺着指引望去,只见村民用机动三轮车牵引着碌碡,在村边巴掌大的麦场里碾压打麦的场面,内心不禁一阵激动。那些亲身经历过的打麦劳动画面,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引发强烈的触动。
过去陕北农村人最憧憬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打麦时节。因为打了麦,就意味着能吃上白生生、虚堂堂、香喷喷的白面馍馍,还有那筋道十足的肉臊子汤白面饸饹了!但农村人都知道,在“麦黄糜黄,秀女下床”的龙口夺食季节,打麦就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容不得半点拖拉,其紧张劳累程度不亚于其他农事活动。
打麦首先要选个红日当头的好日子。提前一天就得把麦场里的坑洼地面用黄土垫平压实扫净,俗称“漫场”或“平场”,确保打麦时颗粒归仓。接着在村民换工或变工帮忙下,解开麦捆,用木杈将麦子抖散铺在麦场上暴晒三四个小时,期间还要反复翻晒,直到麦秆脆响、麦粒一碰就掉才开始打麦。
过去生产力落后时,人们用梿枷打麦。三四个村民戴着草帽或拢着白毛巾,面对面站立,此起彼伏地挥舞梿枷,“啪——啪——啪——”的节奏声吓得偷吃的麻雀四散飞起。后来改用牲口拉碌碡,戴着“愁子”的毛驴或骡马在主人吆喝下转着圈碾压。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开始用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虽然发生过伤人事故,但确实提高了效率。包产到户后,脱粒机渐渐退出,又回到牲口或拖拉机拉碌碡的方式。那时每个麦场边都放着几口盛满水的大瓷瓮,以防火灾,可见农民的消防意识之强。
经过几轮脱粒,村民用木杈将麦秸挑起抖净,堆成圆帽状的麦秸垛,一丈多高的麦秸垛成了判断收成的标志。待麦子堆成圆锥形,人们就到树荫下喝水歇息。下午太阳西斜时,最精彩的扬场表演便开始了。只见一位老把式操起木锨,走到麦堆旁,仰头望天,噘起嘴唇,吹出一连串“嘘——嘘——嘘——”的尖锐口哨。说来也怪,这哨声刚落,一阵清风便应声而来,掠过麦场上空。手持木锨的村民顺势抄起一锨麦子,手臂一扬,金黄色的麦粒便如雨点般唰唰落下,而那些轻飘飘的麦衣则随风飘向远方。另外一个村民手持扫帚,弯着腰,左右开弓,将混杂在麦粒中的麦衣、麦秸和杂草一一扫除。两人一扬一扫,配合得天衣无缝。经过这番紧张而有序的劳作,村民们辛苦一年的劳动果实终于完美呈现。男主人将木锨往麦堆上一插,抹去额头的汗水,惬意地靠在麦堆上,跷起二郎腿,眯着眼睛哼起小曲,俨然一副幸福满足惬意舒坦的模样。女主人则笑吟吟地拿来量斗和麻袋,轻轻放在麦堆旁边,眼里满是丰收的喜悦……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黄河沿岸几个县的小麦种植面积大幅度缩水,逐步让位经济林木。具有传统农耕文明历史的小麦播种和打麦场景,已渐渐消失在视野中,成为民俗专家追寻的对象。回想当年三夏时节,陕北农村旱塬上、梁峁上、坡畖上、川道上大块大块的麦田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波涛般翻涌,人们戴着草帽,你追我赶低头弯腰割麦时“嚓嚓嚓”的镰刀悦耳动听的声音如今已成绝唱,而村小学的学生娃娃们在老师的组织带领下,提着筐子背着水壶,跟在割麦子的队伍屁股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的快乐劳动场面,亦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画卷。
离开苏亚河村时,我不禁回望那片打麦场。只见两个年过半百的村民仍在辛勤劳作,他们佝偻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单。村头的梅杏树依旧硕果累累,红黄相间的果实散发着甜蜜的芬芳。可是,那曾经铺天盖地的金色麦浪,如今又在何方呢?
正值梅杏成熟的季节,我与几个文友沿着黄河岸边乡村采风。忽然有人指着远处惊喜地喊道。顺着指引望去,只见村民用机动三轮车牵引着碌碡,在村边巴掌大的麦场里碾压打麦的场面,内心不禁一阵激动。那些亲身经历过的打麦劳动画面,异常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引发强烈的触动。
过去陕北农村人最憧憬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打麦时节。因为打了麦,就意味着能吃上白生生、虚堂堂、香喷喷的白面馍馍,还有那筋道十足的肉臊子汤白面饸饹了!但农村人都知道,在“麦黄糜黄,秀女下床”的龙口夺食季节,打麦就是一场速战速决的战斗,容不得半点拖拉,其紧张劳累程度不亚于其他农事活动。
打麦首先要选个红日当头的好日子。提前一天就得把麦场里的坑洼地面用黄土垫平压实扫净,俗称“漫场”或“平场”,确保打麦时颗粒归仓。接着在村民换工或变工帮忙下,解开麦捆,用木杈将麦子抖散铺在麦场上暴晒三四个小时,期间还要反复翻晒,直到麦秆脆响、麦粒一碰就掉才开始打麦。
过去生产力落后时,人们用梿枷打麦。三四个村民戴着草帽或拢着白毛巾,面对面站立,此起彼伏地挥舞梿枷,“啪——啪——啪——”的节奏声吓得偷吃的麻雀四散飞起。后来改用牲口拉碌碡,戴着“愁子”的毛驴或骡马在主人吆喝下转着圈碾压。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时,开始用柴油机带动的脱粒机,虽然发生过伤人事故,但确实提高了效率。包产到户后,脱粒机渐渐退出,又回到牲口或拖拉机拉碌碡的方式。那时每个麦场边都放着几口盛满水的大瓷瓮,以防火灾,可见农民的消防意识之强。
经过几轮脱粒,村民用木杈将麦秸挑起抖净,堆成圆帽状的麦秸垛,一丈多高的麦秸垛成了判断收成的标志。待麦子堆成圆锥形,人们就到树荫下喝水歇息。下午太阳西斜时,最精彩的扬场表演便开始了。只见一位老把式操起木锨,走到麦堆旁,仰头望天,噘起嘴唇,吹出一连串“嘘——嘘——嘘——”的尖锐口哨。说来也怪,这哨声刚落,一阵清风便应声而来,掠过麦场上空。手持木锨的村民顺势抄起一锨麦子,手臂一扬,金黄色的麦粒便如雨点般唰唰落下,而那些轻飘飘的麦衣则随风飘向远方。另外一个村民手持扫帚,弯着腰,左右开弓,将混杂在麦粒中的麦衣、麦秸和杂草一一扫除。两人一扬一扫,配合得天衣无缝。经过这番紧张而有序的劳作,村民们辛苦一年的劳动果实终于完美呈现。男主人将木锨往麦堆上一插,抹去额头的汗水,惬意地靠在麦堆上,跷起二郎腿,眯着眼睛哼起小曲,俨然一副幸福满足惬意舒坦的模样。女主人则笑吟吟地拿来量斗和麻袋,轻轻放在麦堆旁边,眼里满是丰收的喜悦……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黄河沿岸几个县的小麦种植面积大幅度缩水,逐步让位经济林木。具有传统农耕文明历史的小麦播种和打麦场景,已渐渐消失在视野中,成为民俗专家追寻的对象。回想当年三夏时节,陕北农村旱塬上、梁峁上、坡畖上、川道上大块大块的麦田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波涛般翻涌,人们戴着草帽,你追我赶低头弯腰割麦时“嚓嚓嚓”的镰刀悦耳动听的声音如今已成绝唱,而村小学的学生娃娃们在老师的组织带领下,提着筐子背着水壶,跟在割麦子的队伍屁股后面捡拾遗落的麦穗的快乐劳动场面,亦成为不可复制的历史画卷。
离开苏亚河村时,我不禁回望那片打麦场。只见两个年过半百的村民仍在辛勤劳作,他们佝偻的身影在夕阳下显得格外孤单。村头的梅杏树依旧硕果累累,红黄相间的果实散发着甜蜜的芬芳。可是,那曾经铺天盖地的金色麦浪,如今又在何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