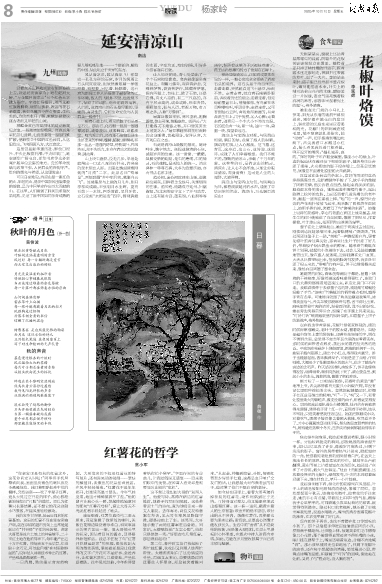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10月10日
红薯花的哲学
“ 你老家可是有名的红薯之乡,这花你肯定认识吧!”同事将手机屏幕转向我,画面里淡紫色的喇叭状花朵盈盈绽放。我盯着那酷似牵牛花的模样,突然语塞——吃了半辈子红薯,竟从未见过它开花的样子,满心都是被地域知识“打脸”的尴尬。原以为红薯只长藤结薯,却不想它的花朵这般小巧雅致,在晨风里轻轻颤动。
我的家乡甘谷驿,是远近闻名的红薯基地。这里的红薯不仅在延安家喻户晓,就连京城的超市货架上也常能见到印有“甘谷驿”字样的包装箱。老家大哥便是这片土地上的种薯能手,二十亩红土地在他的侍弄下,每年能产出近十万斤红薯。按每亩五千元估算,年进账十余万元,可他总自嘲“在村里刚够温饱”,说年轻人用新技术种出的红薯,产量和品质都更胜一筹。
一日清晨,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大哥发来的不仅是红薯花的特写照片,还有段晃动的视频——翠绿的藤蔓间,淡紫色的花朵沾着晨露,在风中轻轻摇曳。“红薯花不是年年都开,得连续高温才冒头。今年气候反常,地里才稀稀落落开了些。”他的留言让我心头一暖,想起昨晚随意问的那句“红薯花啥样”,竟让大哥天不亮就扛着手机钻进了地头。
凑近细看,红薯花直径约三至五厘米,花冠像极了微缩版的喇叭,淡紫色花瓣边缘泛着珍珠白,和同事展示的图片如出一辙。但大哥镜头里的花朵,因沾着田间的露水,显得格外娇艳鲜活。我忍不住发了句“红薯开花财运到家”的祝福,很快收到大哥的微笑表情,紧接着却是段让我意外的文字:“开花可不是好事,会抢养分,让红薯木质化,口感变差,产量也跟着跌。往年见花就掐,今年难得留着给你拍个稀罕。”字里行间的专业劲儿,让我既佩服又感慨——原来我们眼中的美景,在种薯人看来却是需要及时止损的“危机”。
这不禁让我想起大哥的“双面人生”。他爱写诗,常蹲在路边的红薯摊前,就着手机写田间见闻。这些带着泥土气的诗句,竟为他吸引来一群文人朋友。去年寒冬,两位文友特意驱车拜访,见大哥在寒风里跺脚守摊,硬是拉他上了车。谈笑间,大哥随手搬了两箱红薯塞进后备箱。回家后,大嫂嗔怪他“太实心眼”,他却只是憨憨一笑:“好朋友吃几箱红薯,那是瞧得起咱!”
第二年,春种时文友们挽起袖子帮忙栽红薯,秋收时又利用人脉帮忙带货。大嫂渐渐明白了这份情谊的分量,再遇文友来访,总要挑最甜的红薯往人怀里塞,却总被笑着推回来。“从起垄、种植到挖薯、分拣,每颗红薯至少得经手七遍,这都是血汗呐!”文友们的话,让我想起大哥布满老茧的双手,也读懂了他们不愿白拿的坚持。
如今站在田埂上,看着大哥弯腰掐掉新发的红薯花,动作利落到近乎无情。可转身面对朋友,他又能豪爽地送出整箱红薯。这一掐一送间,藏着庄稼人的生存智慧:该舍弃的绝不留恋,该付出的从不吝啬。就像红薯花,再艳丽也要为果实让路;而情谊,总要真心浇灌才能收获长久。生活中的“舍得”从不是简单的权衡,而是像大哥那样,在泥土里耕耘时心怀果敢,在烟火中待人时满含赤诚,如此,方能在岁月里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与温暖。
我的家乡甘谷驿,是远近闻名的红薯基地。这里的红薯不仅在延安家喻户晓,就连京城的超市货架上也常能见到印有“甘谷驿”字样的包装箱。老家大哥便是这片土地上的种薯能手,二十亩红土地在他的侍弄下,每年能产出近十万斤红薯。按每亩五千元估算,年进账十余万元,可他总自嘲“在村里刚够温饱”,说年轻人用新技术种出的红薯,产量和品质都更胜一筹。
一日清晨,微信提示音突然响起。大哥发来的不仅是红薯花的特写照片,还有段晃动的视频——翠绿的藤蔓间,淡紫色的花朵沾着晨露,在风中轻轻摇曳。“红薯花不是年年都开,得连续高温才冒头。今年气候反常,地里才稀稀落落开了些。”他的留言让我心头一暖,想起昨晚随意问的那句“红薯花啥样”,竟让大哥天不亮就扛着手机钻进了地头。
凑近细看,红薯花直径约三至五厘米,花冠像极了微缩版的喇叭,淡紫色花瓣边缘泛着珍珠白,和同事展示的图片如出一辙。但大哥镜头里的花朵,因沾着田间的露水,显得格外娇艳鲜活。我忍不住发了句“红薯开花财运到家”的祝福,很快收到大哥的微笑表情,紧接着却是段让我意外的文字:“开花可不是好事,会抢养分,让红薯木质化,口感变差,产量也跟着跌。往年见花就掐,今年难得留着给你拍个稀罕。”字里行间的专业劲儿,让我既佩服又感慨——原来我们眼中的美景,在种薯人看来却是需要及时止损的“危机”。
这不禁让我想起大哥的“双面人生”。他爱写诗,常蹲在路边的红薯摊前,就着手机写田间见闻。这些带着泥土气的诗句,竟为他吸引来一群文人朋友。去年寒冬,两位文友特意驱车拜访,见大哥在寒风里跺脚守摊,硬是拉他上了车。谈笑间,大哥随手搬了两箱红薯塞进后备箱。回家后,大嫂嗔怪他“太实心眼”,他却只是憨憨一笑:“好朋友吃几箱红薯,那是瞧得起咱!”
第二年,春种时文友们挽起袖子帮忙栽红薯,秋收时又利用人脉帮忙带货。大嫂渐渐明白了这份情谊的分量,再遇文友来访,总要挑最甜的红薯往人怀里塞,却总被笑着推回来。“从起垄、种植到挖薯、分拣,每颗红薯至少得经手七遍,这都是血汗呐!”文友们的话,让我想起大哥布满老茧的双手,也读懂了他们不愿白拿的坚持。
如今站在田埂上,看着大哥弯腰掐掉新发的红薯花,动作利落到近乎无情。可转身面对朋友,他又能豪爽地送出整箱红薯。这一掐一送间,藏着庄稼人的生存智慧:该舍弃的绝不留恋,该付出的从不吝啬。就像红薯花,再艳丽也要为果实让路;而情谊,总要真心浇灌才能收获长久。生活中的“舍得”从不是简单的权衡,而是像大哥那样,在泥土里耕耘时心怀果敢,在烟火中待人时满含赤诚,如此,方能在岁月里收获属于自己的丰硕与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