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12月14日
裹着泥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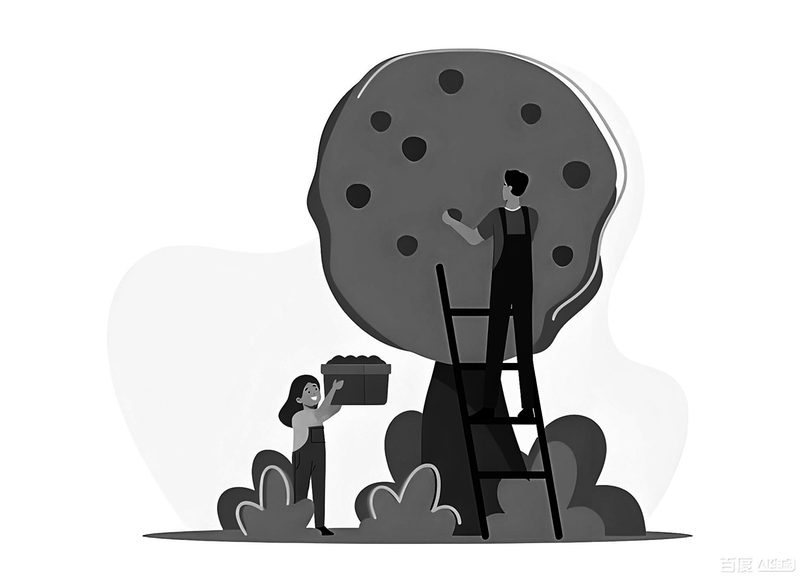
村口的老苹果园还裹在晨雾里,父亲扛着锄头,裤脚卷到膝盖,胶鞋踩进湿润的泥土,像一尾鱼,悄无声息地游进一年中最漫长的守望里。我跟在他身后,踩着他深浅不一的脚印,忽然懂得——原来幸福从不是枝头唾手可得的甜,而是要在泥土里,一寸寸丈量的辛苦。
疏果的时节,他抓起我的手,按在一颗半大的苹果上。“摸这儿。”他的指尖带着果枝留下的细小划伤,粗糙地蹭过我的手背,指缝里嵌着洗不净的泥,“果柄周围软软的,向阳面泛着粉,这才是好果子。”一上午都在弯腰、掐尖、取舍,他疏过的树枝,苹果间距匀称得像精心编排的音符,而他的指关节,却肿得发红,像熟透的樱桃。“好果子要吃饱阳光,吃的时候,甜才会从舌尖,暖到心里。”
国庆的雨,缠缠绵绵,不知疲倦地下着,偏偏赶在卸袋的当口。父亲披着雨衣蹲在树下,手指勾住纸袋的铁丝圈,一拧,一扯,动作轻得像怕惊醒香甜的梦。雨水顺着帽檐流进衣领,他胡乱抹把脸,又去攀扯下一个苹果袋。在高大茂盛的苹果树下,原本高大的父亲,显得那么渺小。可是辛勤和汗水,却让果树一棵棵臣服,为他铸造甜蜜的幸福。
摘果的十月,是果园最热闹也最辛苦的日子。父亲总在凌晨五点就起身摘果、拾筐。他踮脚够向枝桠,掌心托住苹果底部,拇指抵住果柄轻轻一拧,果子便落进筐里,动作轻得没惊扰一片树叶。随后他将刚卸下的苹果轻放进筐,一颗颗苹果宛如易碎的月光,需得小心谨慎。裤脚早被泥水浸透,紧紧贴在腿上,后背溅满了泥点子,他却转头催我:“快把筐挪到屋檐下,别让雨打坏了这些宝贝。”休息时,他坐在树下,顺手捡起一个被小鸟啄过的果子,在衣服上随意蹭两下,便大口咬下去。见我望他,他立刻在果筐里翻找,挑出最大最红的那个塞给我:“按爸教你的摸,果柄软不软?这是园里最甜的一颗。”我咬下一口,汁水顺着嘴角流下。他蹲在一旁,啃着带疤的小果,眼角的皱纹里,飘出淡淡的苹果香。
分拣时,他把最大最红的果子仔细装箱,在箱角工整地写下“女儿学费”四个字,一笔一画,描得格外认真。“等这批卖了,就给你买双新运动鞋。”他边扯紧胶带边说,“刺啦”一声的胶带闪着光。
昨天整理仓库,我在柴房的角落发现了他换下的旧胶鞋,鞋底裂开一道大口,像张着嘴诉说着什么,鞋帮上还沾着去年的泥巴和苹果的清苦香,就像他手上那层洗不掉的老茧。我悄悄拿去搓洗了一遍又一遍,可鞋缝里,始终有洗不净的污泥。
空灵澄澈的月光静静落在那双裂开的旧胶鞋上,像一句沉淀了岁月的感谢。我终于读懂,父亲把整个秋天,把他所有的爱,都揉进了这满园的苹果树里。他教给我的,不只是如何判断苹果甜不甜,更是将辛苦揉进每一个苹果的细处。
(指导老师 井翠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