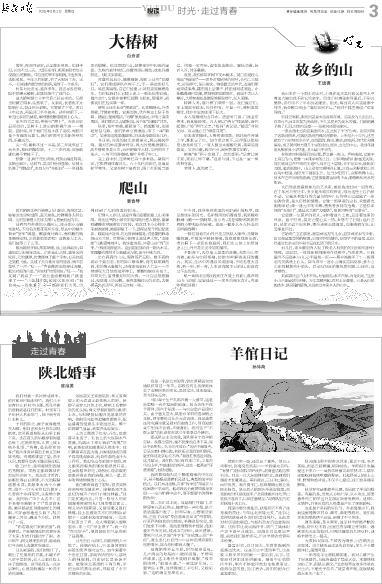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8月03日
大椿树
曾经,每次回老家,总是脚步匆匆。短则半日,长也不过三天。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着母亲说说话,吃顿饭。单位里的事不容耽搁,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今年三月退休,有了大把闲工夫。这不,一回来就拾掇母亲的院落,竟待了一个多月。
村东有处老宅,废弃多年。我去寻些旧物,院中那棵大椿树,却猛地揪住了我的心。
这大椿树是七十年代自己长出来的。记得当时嫌它碍事,险些砍了。父亲说,长着也不太影响什么,就让它长着吧。它便留了下来。四五十年过去,再见时已亭亭如盖。站在树荫下,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如同暖流般缓缓涌上心头。
家乡的方言里,椿树叫“樗卜”。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树干上渗出的黏稠汁液——樗胶。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樗胶可是个有趣的玩意儿,我们经常用它来黏各种东西,乐趣无穷。
头一年,椿树不过一米高;第二年就窜到了两米多,枝桠四散伸展。十二三岁的我,即使踮脚也够不着枝干了。
惊蛰一过,树干泛出青绿,枝条由橘红转黄,又抽出嫩叶。这时节,昆虫们纷纷登场。椿树上趴满了“樗媳妇”,也有人叫“花媳妇”——实则是斑衣蜡蝉。幼虫黑底白点,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大些的通体艳红,点缀着黑白斑纹;成虫后翅鲜红,飞起来如彩虹。
孩童时玩具少,蝴蝶难捉,便盯上这些“花媳妇”。它们常成群趴在树干上,手一捂就能捉几只。装进玻璃瓶,看它们乱撞,小妹总要哭闹着放生。有时候我们在它腿上系上一根长长的白线,抛向空中,它便扑棱着红翅膀飞起来,那情形,就像我们在放风筝一样。
椿树上还生长着“樗老汉”。比苍蝇略大,外壳黑硬,背皱如老脸。它善伪装,伏在树皮上似干鸟粪。硬碰它便缩成团,“咕噜”坠地装死,半晌才鬼祟爬回。我们嫌它丑,沾着树臭,远不如“花媳妇”讨喜。
秋至,椿叶转黄,簌簌落下。拾起断枝,连接处形似马蹄。我们举着它满地跑,印下一串“蹄印”。父亲说这枝条能辟邪,自此走夜路胆壮几分。
冬日里,光秃的枝头挂着果实,风过飒飒作响。菱形的种皮裹着籽实,风大时便翻滚飘远。故乡椿树多是自生,有用的留作木材,无用的当了柴火。山沟里的野椿树,嫩叶多喂了牲口。
我上高中时,这椿树已有十多米高。暑假回家,它张臂遮住毒日头。八十年代的农村,电扇是稀罕物件。父亲在树下垒砖台,搁上水泥板当饭桌。傍晚一家围坐,边吃饭边纳凉。暑热消散,闲话入耳,其乐融融。
夜里,我们姊妹在树下支木板床。某日忽见枝头结出“樗姑姑”——家乡对椿树果的称呼,长约二三厘米,形似柳叶,呈长梭状。物质匮乏的年代,女孩们用线穿成果串,戴在腕上是镯子,挂在颈间成项链。小妹戴着满村炫耀,惹得别家姑娘眼红。我虽不舍让人攀折,大椿树却总是憨厚地摇晃枝叶,任人采撷。
转瞬入冬,落叶积了厚厚一层。我扫拢它们,在上面踩来踩去,沙沙作响。年复一年,椿树愈发粗壮,我亦在它的注视下长大。
乡人视椿树为吉祥木。盖房时门扇、门框必用椿木,谓其能辟邪。古人更以“椿寿”喻高龄,唐代起便以“椿”指代父亲。“椿庭”表父恩,“椿萱”并称父母。双亲健在曰“椿萱并茂”。
后来老家搬迁,大椿树被遗落。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渐渐忘了它。如今重立树下,总浮现这般场景:葱茏树冠下,一家人围坐水泥板吃饭,孩童追逐嬉戏。父亲已逝,我亦白头,而树影婆娑如昨。
树离“家”四十余载了。忽然想到:“活着让树守家,死后让树守墓。”这家与园,不过是一屋一树的相守罢。
老樗卜,真的老了。
村东有处老宅,废弃多年。我去寻些旧物,院中那棵大椿树,却猛地揪住了我的心。
这大椿树是七十年代自己长出来的。记得当时嫌它碍事,险些砍了。父亲说,长着也不太影响什么,就让它长着吧。它便留了下来。四五十年过去,再见时已亭亭如盖。站在树荫下,一种无比亲切的感觉,如同暖流般缓缓涌上心头。
家乡的方言里,椿树叫“樗卜”。而我记忆最深刻的,是树干上渗出的黏稠汁液——樗胶。那时候,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樗胶可是个有趣的玩意儿,我们经常用它来黏各种东西,乐趣无穷。
头一年,椿树不过一米高;第二年就窜到了两米多,枝桠四散伸展。十二三岁的我,即使踮脚也够不着枝干了。
惊蛰一过,树干泛出青绿,枝条由橘红转黄,又抽出嫩叶。这时节,昆虫们纷纷登场。椿树上趴满了“樗媳妇”,也有人叫“花媳妇”——实则是斑衣蜡蝉。幼虫黑底白点,就像夜空中闪烁的星星。大些的通体艳红,点缀着黑白斑纹;成虫后翅鲜红,飞起来如彩虹。
孩童时玩具少,蝴蝶难捉,便盯上这些“花媳妇”。它们常成群趴在树干上,手一捂就能捉几只。装进玻璃瓶,看它们乱撞,小妹总要哭闹着放生。有时候我们在它腿上系上一根长长的白线,抛向空中,它便扑棱着红翅膀飞起来,那情形,就像我们在放风筝一样。
椿树上还生长着“樗老汉”。比苍蝇略大,外壳黑硬,背皱如老脸。它善伪装,伏在树皮上似干鸟粪。硬碰它便缩成团,“咕噜”坠地装死,半晌才鬼祟爬回。我们嫌它丑,沾着树臭,远不如“花媳妇”讨喜。
秋至,椿叶转黄,簌簌落下。拾起断枝,连接处形似马蹄。我们举着它满地跑,印下一串“蹄印”。父亲说这枝条能辟邪,自此走夜路胆壮几分。
冬日里,光秃的枝头挂着果实,风过飒飒作响。菱形的种皮裹着籽实,风大时便翻滚飘远。故乡椿树多是自生,有用的留作木材,无用的当了柴火。山沟里的野椿树,嫩叶多喂了牲口。
我上高中时,这椿树已有十多米高。暑假回家,它张臂遮住毒日头。八十年代的农村,电扇是稀罕物件。父亲在树下垒砖台,搁上水泥板当饭桌。傍晚一家围坐,边吃饭边纳凉。暑热消散,闲话入耳,其乐融融。
夜里,我们姊妹在树下支木板床。某日忽见枝头结出“樗姑姑”——家乡对椿树果的称呼,长约二三厘米,形似柳叶,呈长梭状。物质匮乏的年代,女孩们用线穿成果串,戴在腕上是镯子,挂在颈间成项链。小妹戴着满村炫耀,惹得别家姑娘眼红。我虽不舍让人攀折,大椿树却总是憨厚地摇晃枝叶,任人采撷。
转瞬入冬,落叶积了厚厚一层。我扫拢它们,在上面踩来踩去,沙沙作响。年复一年,椿树愈发粗壮,我亦在它的注视下长大。
乡人视椿树为吉祥木。盖房时门扇、门框必用椿木,谓其能辟邪。古人更以“椿寿”喻高龄,唐代起便以“椿”指代父亲。“椿庭”表父恩,“椿萱”并称父母。双亲健在曰“椿萱并茂”。
后来老家搬迁,大椿树被遗落。那时我在外地上学,渐渐忘了它。如今重立树下,总浮现这般场景:葱茏树冠下,一家人围坐水泥板吃饭,孩童追逐嬉戏。父亲已逝,我亦白头,而树影婆娑如昨。
树离“家”四十余载了。忽然想到:“活着让树守家,死后让树守墓。”这家与园,不过是一屋一树的相守罢。
老樗卜,真的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