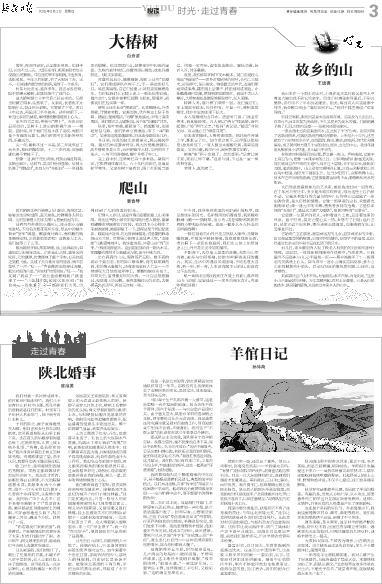发布日期:2025年08月03日
故乡的山
我出生在一个很小的山村,小得在延川县行政区划图上拿着放大镜也找不到它的名字。但我们村离张家河很近,不到五里路,步行用不了半小时就能到。因此,每当有人问我是哪个村的,我会脱口而出:“离张家河不远。”有时干脆直接说:“张家河的。”
自我记事起,张家河就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年代后又恢复为乡政府,不久又更名为延水关镇。门前的牌子换了几回,但地方没变——张家河还是张家河。
一条由西北方向流来的河水,在此拐了个“S”形弯。张家河因了这条河得名,也因这条河的滋润而繁荣。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就有了六年制完全小学,还有医院、商店、粮站、邮电所、信代社和兽医站,成了黄河畔方圆几十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当年就是从张家河小学毕业,考入延川中学的。
在张家河村最显眼的位置,矗立着一座山。严格来说,它算不上真正的山,更像一座孤零零的土丘。它和周围的山脉毫无关联,突兀地耸立在开阔的川道中,高不过十层楼,长不足百米,陡峭如刀削,笔直似旗杆。山上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只有无名野草和山花在风中摇曳,在阳光下倔强生长。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山头,河水在它背后缓慢流淌,它就像披着金纱的少女,静静聆听河水的絮语。
大自然是最富想象力的艺术家,能创造出世间一切奇观。在千年河川变迁中,多少泥沙被冲刷带走,唯有这座土丘岿然不动。它蕴含着怎样的力量与精神?它的存在已超越了一座山的价值,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像一部厚重的史书,承载着光阴的印记;像一座无字的丰碑,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它是张家河的“天安门”,是延水关的“大雁塔”,是黄河畔的“宝塔山”。
它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守护着这片土地,见证着这里的兴衰。游子归来,望见它便心头一热,乡愁有了归处;远行之时,记住它就不忘来路,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能辨明方向,知道根在何处。
它始终伫立在那里,遥望着远方的儿女,盘算着家乡的未来。它记得这里曾经的辉煌,记得农民的勤劳,记得学子的奋发,也记得那位北京来的年轻书记在此洒下的汗水。
前几日,家乡群里有人发了段无人机航拍的《张家河新村》视频。画面里,一排排新窑洞掩映在绿树中,气派非常。可我遍寻不见那座小山,心里猛地一沉——莫非被推平了?一股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如今推平一座小山确实易如反掌,多少山头在机械轰鸣中消失。后来得知是拍摄角度问题,山还在,这才释然。
刘禹锡诗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座小山正是最好的诠释。万丈高楼易起,百尺土丘难移。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灵魂的图腾,永远屹立在家乡人的心中。
自我记事起,张家河就是乡政府所在地。后来改为人民公社,改革年代后又恢复为乡政府,不久又更名为延水关镇。门前的牌子换了几回,但地方没变——张家河还是张家河。
一条由西北方向流来的河水,在此拐了个“S”形弯。张家河因了这条河得名,也因这条河的滋润而繁荣。上世纪六十年代,这里就有了六年制完全小学,还有医院、商店、粮站、邮电所、信代社和兽医站,成了黄河畔方圆几十里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当年就是从张家河小学毕业,考入延川中学的。
在张家河村最显眼的位置,矗立着一座山。严格来说,它算不上真正的山,更像一座孤零零的土丘。它和周围的山脉毫无关联,突兀地耸立在开阔的川道中,高不过十层楼,长不足百米,陡峭如刀削,笔直似旗杆。山上没有可耕种的土地,只有无名野草和山花在风中摇曳,在阳光下倔强生长。每当夕阳西下,余晖洒满山头,河水在它背后缓慢流淌,它就像披着金纱的少女,静静聆听河水的絮语。
大自然是最富想象力的艺术家,能创造出世间一切奇观。在千年河川变迁中,多少泥沙被冲刷带走,唯有这座土丘岿然不动。它蕴含着怎样的力量与精神?它的存在已超越了一座山的价值,是大自然的馈赠。它像一部厚重的史书,承载着光阴的印记;像一座无字的丰碑,镌刻着岁月的沧桑。它是张家河的“天安门”,是延水关的“大雁塔”,是黄河畔的“宝塔山”。
它更像一位慈祥的老人,守护着这片土地,见证着这里的兴衰。游子归来,望见它便心头一热,乡愁有了归处;远行之时,记住它就不忘来路,哪怕走到天涯海角,也能辨明方向,知道根在何处。
它始终伫立在那里,遥望着远方的儿女,盘算着家乡的未来。它记得这里曾经的辉煌,记得农民的勤劳,记得学子的奋发,也记得那位北京来的年轻书记在此洒下的汗水。
前几日,家乡群里有人发了段无人机航拍的《张家河新村》视频。画面里,一排排新窑洞掩映在绿树中,气派非常。可我遍寻不见那座小山,心里猛地一沉——莫非被推平了?一股莫名的失落涌上心头。如今推平一座小山确实易如反掌,多少山头在机械轰鸣中消失。后来得知是拍摄角度问题,山还在,这才释然。
刘禹锡诗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座小山正是最好的诠释。万丈高楼易起,百尺土丘难移。它是大自然的杰作,是灵魂的图腾,永远屹立在家乡人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