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日期:2025年08月17日
黄土高坡上的山丹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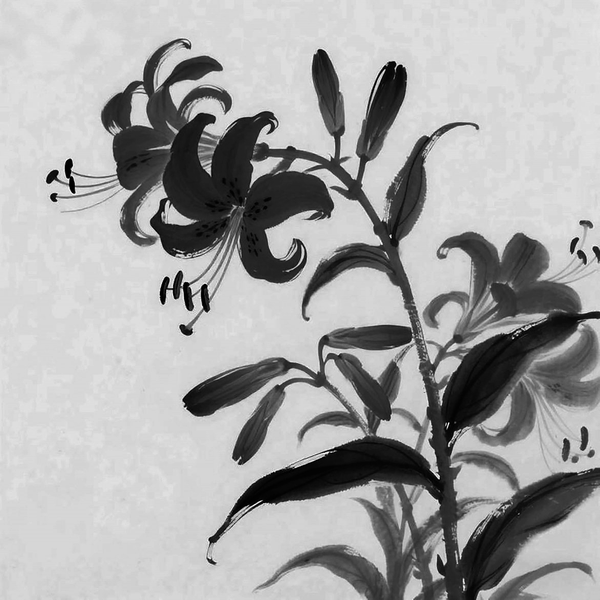
我写下山丹丹这三个字,笔尖便像沾了火,纸页也似被“哧啦”一声灼出一条红痕。整整十二年,我在陕北的沟沟峁峁里滚爬行走,喝过最烈的糜子酒,唱过最酸的信天游,可只要闭上眼,最先跳出来的还是那一簇簇火苗般的山丹丹。它不是花,是陕北的魂,是被黄土高坡埋了半截还在仰头笑的一株株红精灵。
五月的陕北,风还带着小刀子。塬畔的草刚冒头,就被风像掐着脖子似的按回土里。就在这时候,山丹丹从酸枣刺、驴蹄窝里、塌了一半的墓圪崂旁、背洼处,冷不丁地探出一支支细长的小绿胳膊。那叶子绿格英英,像十七八的后生,骨头里憋着要炸裂的劲儿。再过半月,顶端便“噗”地吐出一粒火星,火星越烧越大,烧成一盏盏倒挂的小红灯笼,红格英英。
我第一次见它是在后洼梁。那天我跟着队长去修水坝,铁锹把震裂了虎口,血顺着木柄往下爬。队长忽然扯着嗓子喊:“北京娃,快看!”——坡底一丛山丹丹正开在悬崖边,风把花瓣撕成碎绸子,可那红反倒更艳了,像要替我把手上的血再烧沸一次。我愣在那儿,队长用烟袋锅子敲我后脑勺:“这叫山丹丹,咱陕北最美的婆姨花!”
陕北人把山丹丹唱进信天游,调子一甩,那股劲儿仿佛能把天剐下一层皮。汉子们唱:“山丹丹开花背洼洼红,看见妹妹就想死个人。”女子们回:“山丹丹开花一溜溜鲜,哪搭搭想起哥哥哪搭搭酸。”词粗,可那红是真红,酸也是真酸。
那些婆姨、女子们爱凑在一块儿纳鞋底,常把山丹丹的模样绣在鞋垫上。一针扎下去,红线在白布上蹦跳,像雪地里猛地蹿起团火。绣到花心时,总要将两股线拧成一股,说这样“心才实,男人走西口也不怕”。有个小女子手一抖绣歪了针脚,好好的花骨朵成了歪嘴石榴,婆姨们笑得前仰后合:“莫不是看上北京娃了?不想再困在这山沟沟里喽?”那女子脸涨得像山丹丹,啐道:“谁瞎琢磨谁就是吃屎的瓜娃娃!”
山丹丹开得最盛时,窑洞的窗户就成了天然画框。天刚蒙蒙亮,第一缕光准先落在窗棂那盆移栽的山丹丹上,花瓣薄如刚吹好的糖膜,血丝似的脉络里像淌着光。房东路大娘跪在炕上擦窗,嘴里念叨:“花红得正好,今年雨水足,庄稼定能多收几担。”她满脸皱纹被花映得通红,喜滋滋的,像被山丹丹吻过的黄土沟壑。
有一回我发高烧,满嘴胡话。路大娘把山丹丹的花捣碎,混着蜂蜜灌我,苦得我当场蹦起来。她拍着炕沿笑:“这花是药,专治城里人想家的毛病。”后来查书才知道,山丹丹鳞茎入药,可安神。
七月一场雹子,把一片山的谷子砸成了秃子。我站在崖畔,看见整面坡的山丹丹被冰雹砸得趴了窝,红花瓣嵌进泥里,像被踩灭的烟头。队长蹲在地头抽烟,烟锅子里的火星和残花一同熄灭了。
可第二天早上,那些弯折的茎秆又支棱起来,花瓣被风舔干净,露出更亮的红。队长用镢头挑起一丛给我看:“看见没?根在,魂就在。”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陕北人把山丹丹叫“打不死的红”。它们不是被种下的,是被风刮、被鸟衔、被羊蹄子踢到这里,自己长出来的。就像我们这些知青,说是来“扎根”,其实是被时代的簸箕颠到这里,却也在石缝里扎下了歪歪斜斜的根。
我去延安电厂的那天,全村人送我到大路口。路大娘把一朵刚开的山丹丹别在我扣眼里,花茎别断处渗出乳白的汁,像没有哭出来的泪。队长把烟袋锅子别在裤腰上,第一次用普通话说:“常回来,看花。”
车发动时,我透过蒙尘的后窗看见他们站成一排,像一丛被风刮斜的山丹丹。车转过山峁,我突然发现扣眼里的山丹丹少了一片花瓣——准是大娘掐的,她怕我“把心全带走”。我把那缺了一瓣的山丹丹夹进笔记本。后来它枯干了,艳红褪成了褐黄,可对着光一照,脉络里仿佛还淌着当年的光,簌簌地在纸页间流动。
三十多年后,我从居住的西安,以诗人与作家的身份回陕北。列车穿过隧道,黄土高原已由黄格英英变成了绿格英英。后洼梁已改名“山丹丹景区”,柏油路直通到后洼梁,崖畔修了观景台,也建起了高楼大厦,卖烤土豆、烤串的大娘,她的普通话比我还标准。
我在观景台上找到当年的队长,他牙掉光了,手里攥的烟袋锅子换成了不锈钢保温杯。我指着一丛人工培育的双瓣山丹丹问:“这还是咱当年的种?”他咧嘴笑:“种子是新培育的种子,就是和从前不一样了。”他让我看花心里放置的二维码牌子,说这个是要销往外地的。此时,侧耳听到附近小学里传来《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童声合唱。
我蹲下来抚摸那些花,花瓣比记忆里要厚,红得发腻,像涂了口红。忽见石缝里钻出一株单瓣的,瘦伶伶,却红得野,红得疼。我掏出当年那朵干花的照片比对,颜色竟一模一样。
临走前,我在后沟梁刨了一捧土,连一株山丹丹一起装进搪瓷缸,带了回来。
如今搪瓷缸摆在我的书桌上,鳞茎还在土里发了新芽。老婆问:“能活吗?”我说:“活,肯定活。”这是陕北留给我的永远的记忆与最美好的风景,是一团烧不尽的火,在胸口会一直闪亮。
夜里写稿时望它,似有信天游在唱,还有个声音轻响:“你忘不了黄土高坡,黄土高坡也忘不了你。”这大概就是量子纠缠吧!
